人类怀揣着梦想。让梦想成为现实,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该梦想必须是现实需要的折射。只有立足于满足或者更有效地满足现实需要的梦想才有现实化的可能。其次该梦想的提出正当其时。当鲁班想造出可以让人飞翔的器具时,他的梦想在当时充其量只是幻想,而19世纪末怀特兄弟想造出滑翔机飞上天空,这一想法得益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机械技术的进步而变得可行,他们也因此成为现代飞机之父。第三,要有围绕此一梦想而进行的持续、叠加的努力,这才会使得该梦想成为可见并深刻影响人们的伟大实践的始因。那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科学理论发展或者生活方式状态的梦想此时就提供了上述革命中的“范式”,为后续的一系列思想、行动提供了最初的“念头”。
高铁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始于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的正式通车。建设该高铁的提议则是在2002年2月召开的“京津经济一体化战略研究与建议”课题讨论会上南开大学刘乘镰教授的发言,可以说他是今日中国第一个怀揣高铁梦想的人。作为学者,刘教授多年来关注并跟踪日本、法国为代表的高铁技术领先国家,让他心生在中国建设高铁的清晰思路。原中国铁道部开始将高铁建设列为铁路发展的重要牵引力,制定出“四纵四横”的全国高铁网络布局,中国进入到高铁建设全面提速的时期。高铁建设不仅带动了中国诸多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让民众的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高铁从少数学者的梦想变成了中国铁路“操盘人”(包括决策者、建设者、运营者等)的梦想,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市场需要和政府财政的巨额投入。高铁梦想由此一步步成为现实。
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既有相互增益的正向作用,又有难以克服的相互掣肘。一方面梦想的提出,指引了现实,给现实以激励,又显示了现实的“骨感”,给现实以无情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现实化一旦达成,就远离了梦想,失去了梦想原初的多样可能性,同时维护现实的冲动又会遏制人们进一步提出新梦想,现实化很可能就是梦想的终止符。高铁建设中所蕴含的梦想与现实的关系也有类似的困境。高铁无非是轨道交通的一种方式,是为了更好满足人类出行需要而产生的新技术,它要服务于人类幸福生活的目的。一旦高铁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高铁就成为了人役于物的现代异化形式。
《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的作者戴荣里是亲历了中国高铁建设的参与者,他对高铁的赞美在全书中自然流露,却毫无做作之感。我相信,读者完全理解他的这份感情投入。事实上,《最完美的抵达》也不是一味讴歌,也对其中的败笔有所揭示,例如,对2011年的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全面分析就显示出了作者的冷静和理性。作者融合了技术员、施工者、观察者、写作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对中国高铁梦想的解读就多了几分厚重,全书不仅有对梦想的敬仰,更有对现实的反思。中国高铁建设不能一味高歌猛进,还要有更多的凝重之思和深切之问。在中国高铁经历了近十年的大发展之际,《最完美抵达》一书的问世,就好象米涅玩河畔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了,它要向人们宣示适时的思考,唤起我们去追问技术之善与我们的美好生活之深切关联。这样的追问对于当下中国尤其迫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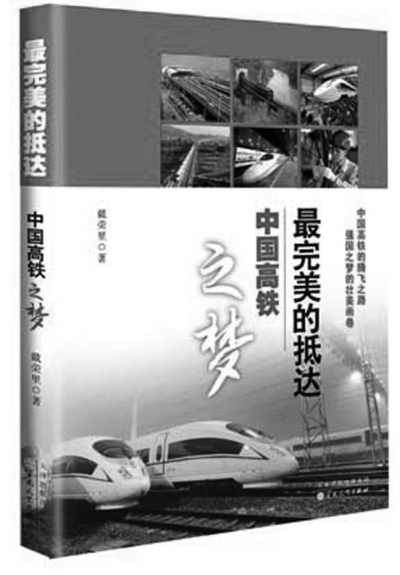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