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比较不亲近的人,背后说我是书呆子;和我比较亲近的人,当面叫我书呆子。人前人后既然有如此共识,我只有供认不讳。
我五岁时,父亲手里捏本“尺牍”,把我送进私塾。我除了能背“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久违慈颜”,同学们读的“人之初,性本善”,“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我也能背。八岁便偷看父亲看的《薛仁贵征东》。《饮冰室文集》也读的很有兴味。
七年中学,学校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读了大半。在图书馆我最喜欢读的是报纸杂志上的批判文章。喷在曾国藩、胡适、尼采、马尔萨斯、凯恩斯……身上的口水很臭,我却闻到了这些人文字中的香气。
走火入魔。我竟然对同桌同学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封建专制,资本主义既然是历史规律中的一个社会时期,那么不可能跨越。可以跨越,那就否定了马列主义的“规律”。咎由自取。高中毕业,教政治课的想恢复党籍的刘副教导主任在我的那份“高考政审表”上签上“不同意录取”,于是我名落孙山。
或许是民主人士衷期星校长怜悯我或者有点欣赏我,也或许是教我们语文的刘世南老师把我的作文常拿出来讲评有了感情,向校长提了建议,衷校长给文教局长写信,推荐我去乡村中学任语文教师。因此,我有了一只洋磁饭碗。很高兴,书没白读,还省了上大学需要的父母血汗钱。
在大学里读书的同学替我找或买了文、史、哲等专业的讲义,我觉得也是在读大学,而且同时是在几所大学里听文、史、哲等学科的教授上课。
文革中“批林批孔”,校长要我给全公社的教师们讲“尊法批儒”。从大礼堂出来,我的脸上落满了老师们惊异的目光。公社干部学哲学,也要我去讲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为占领农村的社会主义文艺舞台,我写些小剧本和小演唱,似乎就有了点知名度。“文革”末,县革委把我从近四千教师中调出来,叫我到县革委政治部宣传组上班。宣传部里,除了领导,都是本科毕业生啊。
我读书,读出了前面的一条大道,一片阳光。我不信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之类的话,只觉得书把我居住的空间挤小了,却把头脑中的世界拓宽了。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因而产生了“恶性循环”。
我的住房里,木箱、纸箱装的是书,床上床下也都码着书。
书的纸张和油墨的气味,使我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种知识和读书的氛围。妻子、孩子也跟着我成了书迷。记得在大孩子读中学时,课余时间都粘在书上,叫他吃饭也不应。我只得去拿掉桌上的书往外走,他的眼睛不离书上的字,让书牵着走到餐桌边,令全家大笑不已。最小的孩子看书看的舍不得睡,我说他,他瞪着一双眼睛和我吵,反讥这一切都是学我的。
大孩子也是五岁入学读书,十五岁以考区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成了北大的教授。
有一年暑假,大孩子从北大寄回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小说和杂志,包裹一打开,全家人一本两本抢过去,都聚精会神读起来。不知谁惊叫一声:“呀,三点半了。”于是,全家一阵大笑,将中餐与晚餐合起来吃,菜根糙米竟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滋味……
邻居们都笑话我们,说一家全是书呆子。
机关大院中的孩子都有一种自豪感,我一家人全是书呆子,头和尾巴都夹在书页中。孩子们不会和人打架斗殴,招惹麻烦;我也把功名利禄看的淡薄了,有了知足常乐的快活,在文联的冷板凳上,心满意足地坐了二十余年。
我们一家人都认为,书让我们获得了知识,知识不仅让我们不去谋虚逐妄,没有患得患失的苦恼,更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从昨天看到了今天和明天,在生活中明白了什么是高尚的实实在在的追求。实在的追求,会使生活充实,更有自尊,还有点自豪。
我的孩子,都有大学本科文凭,有北大的文学博士,也有北京理工大学的硕士。一家子,有教授,有高级工程师,会计师,也有小企业主,成了北京人或深圳人。我这个原本是偏僻山区的贫穷农家孩子知足了。常人觉得我失去的太多,朋友常为我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而不平,我总觉得我因读书得到了常人不易得到的东西,更得到了书给我的情趣和厚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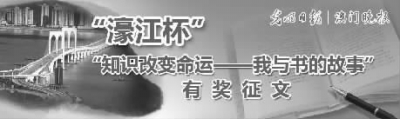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