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汇集了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的随笔。它们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是一些零碎感触的积累,并非什么成熟的结论。也许,正由于不成熟,才成为其存在的理由。
因为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的,任何思想不可能是一旦出现,就成为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即如马克思,他的思想基本定型于19世纪下半叶,迄今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了。假如他仍在世,会不会完全认同他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思想观点字字是真理呢?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断演进着,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
我原来没有写书的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翻译出版过两本苏联的小书——《太阳系的结构学说》和《自然之谜》,都是通俗的科普读物。
当时的学术环境比较特殊,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我刚好在外文书店买到一本法国新版的卢梭《社会契约论》,很喜欢,就翻译出版了。后来商务印书馆找我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可是翻译这本书,却成为我“文革”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终审“罪状”——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那时候的准则是,不问真相就可以给人扣上帽子肆意批判。“文革”后,商务印务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告诉我,这书是毛泽东交译的。
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我参加写宋明理学部分。当时还有几位没有摘“516”(即反革命阴谋集团)帽子的同事,不能参与写作。他们不服气,便另起炉灶,另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发展史》(是我起的书名),也邀我参加,结果我变成了“两面派”。书写成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当时正在做一套对外介绍中国文化的丛书,选了这本,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边译边写。外文社又找我写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这是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钢合作的。
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历史学的书,不是讲历史,而是讲历史学。现在还没有写,以后也许没有精力写了。
历史学界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可是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却处处都在以西方的观点为坐标。例如,根据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到处去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却处处套用西方中心论来衡量中国的文明。我想应该有一本讲历史学的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历史学家反对西方中心论,可是他们却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他们总是问,中国封建历史怎么那么悠久?这是一个典型以西方封建历史为标准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既然反对西方中心论,为什么又要以西方的尺度为准来衡量中国呢?为什么不用中国的尺度为标准,那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反过来了,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历史那么短?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只研究中国封建历史的长期性,为什么不讲西方封建社会的短暂性?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标准。实际上,这些历史学家口头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脑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像中国封建社会时间为什么那么长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这是用西方封建制历史作为标准。
历史学界热衷于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有资本主义,中国也非要有资本主义不可吗?这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想要化解心理上的疙瘩——我们也得要有资本主义,至少是萌芽。我觉得这是心理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学的问题。这是因为学者有心病,总以西方为标准。
其实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社会这一普世的道路。不要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因为普遍性终究是第一位的,而特殊性是第二位的,不能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近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西方比中国先进一步,就是因为他们17世纪先有了近代科学,而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20世纪初叶才真正地接触到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本身并不分东、西,只是西方更早地发现并应用近代科学,而我们却老是把近代科学放在“东”“西”的框架里边来理解。学术研究也像经济发展一样,不能只追求数量,不求质量。总跟人家比,实际上会把自己引到歧路上去,而找不到通向现代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直到“五四”运动才总结出两面旗帜——即科学和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如果仅从字面上,现在大家都熟悉科学与民主,可是做起来为什么又这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例如大跃进时期时亩产多少斤就取决于你胆子的大小,甚至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去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没有人听到农民直接说,亩产没有几万斤。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有那么多农民,就没有听说哪个农民反对。这一点从反面证明了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大跃进时真正讲民主,就不可能造成后来饿死那么多人的大悲剧了。
关于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所起作用,一些研究者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当近代科学已经萌芽的时候,天主教教士来中国是传授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他们并没有近代科学知识,近代科学在中世纪宗教徒看来是异端邪说,从布鲁诺、哥白尼到伽利略这些近代科学的奠基人都受到宗教的迫害。因此,对传教士的作用不能够评价过高,对于科学和文化的近代化而言,这些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价值,没有贡献。直到“五四”时期,我们才真正直面科学与民主。
要走向现代社会,就要接受普世性理念的价值。学术的目标是追求真理,所以不存在东方和西方的差异。都是学术,就只有对错、精粗与高下之分,但并不是中西之别的问题,将它归结到中西文化之不同并不妥当。人道主义也是古今中外都应该遵守的。科学也具有普世性。2+2=4不分古今中外,万有引力定律是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阶级都应遵循的科学规律。不服从科学,就会受到科学的惩罚。要使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无产阶级政治就必须首先尊重科学。否则就会导致对人的不尊重,对生命的不尊重。
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要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民主是近代文明的一大贡献,其作用是能够约束权力的绝对化,使权力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在正确的方向上。绝对权力而不受约束是非常可怕的。当朱元璋是乞丐时,有一碗剩饭给他,他就会满意了。等到他做了皇帝,就大开杀戒,一次残杀就是几万人。蓝玉是他手下大将,杀害蓝玉时,诛连了八万人。朱元璋做乞丐时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想法。等到他做了皇帝,享有绝对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西方出问题也出在不科学、不民主。前车之鉴如德国。德国科学很发达,但不民主,结果出现了希特勒那样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社会进步需要科学和民主。自近代科学问世以来,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空前强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大踏步提高,但在文化思想方面进步并不太明显。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例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但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消除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会导致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缺失。所以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科学和民主。
(本文为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一书的作者自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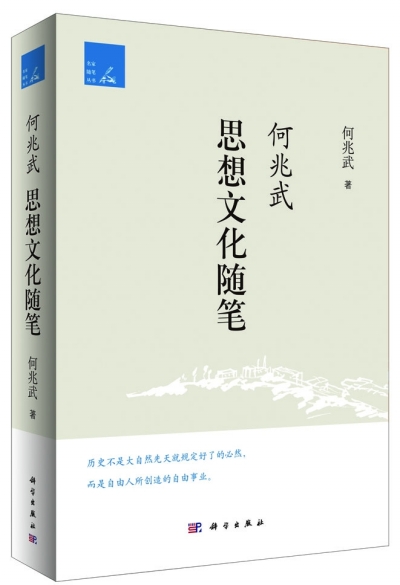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