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个怪圈,执着于作家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却对作家的生平缺乏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很多文学研究者的作家论都显得十分单薄,缺乏对作家本身的关注和了解,因此新时期以来好的作家作品论寥寥可数,而像样子的作家传记更是少得可怜。比如国内周作人研究这几十年来都很热闹,但周作人传记写得最好的居然是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国内只有钱理群十几年前的一本旧作可读。
初春时节,我读到了张耀杰先生的新书《戏里戏外》,感慨终于有一本像样子的曹禺传记可以流传后世了。张耀杰的本业就是戏剧研究,他的老师田本相先生是我国戏剧学界的权威,我曾经听南京大学的董健先生惋惜当年没有把张耀杰招到门下。我之前很少读过张耀杰的戏剧研究著作,反倒是对他的民国人物研究颇感兴趣,他写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系列书,我都一一看过,特色鲜明,在诸多的民国人物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
谢泳先生在这本书的推荐语上写道:“张耀杰写作传记的一大长处,是他不平面地列举材料。他能让人从材料的选择和评价中看出自己的观点,还有就是对传主的负面东西毫不留情。像他这样以解剖的眼光写作传记的,现在还不是很多,所以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认为这恰恰是张耀杰写作最让人欣赏的地方。
张耀杰的这部传记,我认为其中最吸引人的便是对于传主私人生活的追溯,国内的研究者对于民国时代知识人的私人生活极为关注,尤其是胡适,更有余英时先生写下长文钩沉索引,进而成书,洋洋洒洒万言。但是曹禺的私人生活,却极少有人关注,其实他的私人生活,与其创作密不可分,陈白露的原型,便是曹禺的梦中情人王右家。张耀杰指出,曹禺对于陈白露的生活原型王右家曾经有过的不点名的回忆:“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据张耀杰考证,这里所说的“报社总编辑”,指的是1932年1月离开上海到天津任《益世报》社论总撰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后来在反右运动中与章伯钧并称为章罗联盟的罗隆基。
当然,对于传主私生活的回顾并非本书的主题。张耀杰自称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很直接的冲动,就是觉得中国许多时髦学者靠着炒作外国人的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暴得大名,却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愿意扎扎实实地按照结构主义的学术规则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文本细读。
从这一点出发,便可以看到张耀杰此书犹如余英时破解陈寅恪诗歌中的暗码系统一样,对曹禺戏剧中的密码一一破解。这种密码,张耀杰将其归结为运用舶来品的现代话剧和现代电影的文体形式,把鲁迅在《女吊》一文中所说的传统民间戏曲“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的影剧模式,最大限度地扩充改造。张耀杰认为,这种密码模式的特色在于,将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和外国宗教文化的紧密结合,形成了“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
撇开曹禺的作品不谈,曹禺本人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可能更加值得我们去反思。曹禺在1949年之后,曾经多次参与政治运动,从胡风案到反右运动,无一遗漏。张耀杰指出,曹禺在1955年所写的《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而到了反右运动中,当时刚刚入党的曹禺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吴祖光,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这种迷狂的类似于演戏的状态,正符合了《戏里戏外》这一书名对于曹禺的定位。
当然,文革中的曹禺是悲惨的,据曹禺的子女回忆,曹禺当时遭遇到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
新时期之后,曹禺的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他在于1990年代初一首题为《玻璃翠》的短诗中说:“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但是这时的醒悟为之晚矣,曹禺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结。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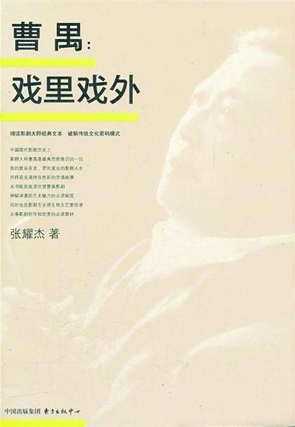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