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拿到王族的散文集《第一页》时,如同暗陷入一片雪野,浓烈的白,让人顿时茫然无措、失去了方向感,内心的惶恐开始逐渐涌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正在看着的这本没有序跋、后记的散文集。在成书时,它的作者对此一无交代,作为读者,我只能通过书中的近40篇文章来找寻答案。
然而,王族在设置一道迷雾时,又迅速给你一把钥匙——即本书的开篇之作《第一页》。读着本书的开篇,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还没来得及涌出的惶恐就被攻击得烟消云散,阅读的心顿时一片澄明。
这种澄明,更多是来源于内心最柔软处的回忆。是啊,谁的人生没有“第一页”?王族的高明在于勇敢地翻过了第一页,并把他写成了文章,尽管在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伤疤,这也让回忆增添了些许的蕴味,变得更悠远,而又经久弥新。
小说家阎连科曾经在阐述故乡对其创作影响时说过,那块土地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你变成一个作家,那块土地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有太多东西需要你去表达、表现,所以他让你成了作家。所以,在读本书中的《第一页》《出走》《偷鱼》《飞贼村》等篇时,我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早已经注定好的,甚至那几篇20多年后被发现的四年级作文,都是冥冥中在等着他,只为让他成为作家。因为父老乡亲赖以生存的故乡,有太多了东西需要王族去表达、表现。
走过一个地方便能爱上这个地方,并能以之为家,献以文字的人是有福的。王族就是这个有福的人。
理所当然地,王族出生、成长的村庄,以及现在生活的新疆;那个“打开青春期骚动'的第一页的放蜂的江苏女人,“告诉我不该淡忘往事”、吃鱼技术一绝的急娃子,甚至是大雨中偶遇的一架马车等都是王族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也是他一切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作为王族童年的关键词之一,“火车”,在青春期的作者经历中意义必定是非同一般的。收入本书的几篇有关火车的文章,真是见功夫的文章。自然而不夸张,不雕琢,不修饰,犹如深夜灯下的一杯白开水,自然而纯净,一片澄明。
孙犁曾说过,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马车翻了》、《唱歌》等都是自然的文章。想来,王族是深谙个中滋味的。
《与诗歌相遇》是书中不起眼的篇章之一。但我却一连读了好几遍。我把他当作了王族留下的另外一把钥匙——在散文之外,王族还是写诗的。没有写诗经历的读者,大约很难明白诗歌对于一个14岁少年的震撼。这种震撼,是改变一生的,甚至连呼吸都是幸福的。也就是这篇文章,一下子把正在阅读的我,拉回到了7年前刚刚拿起笔学写诗歌时的幸福与苦涩。也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和王族同为一个诗歌写作者的共鸣。
布罗茨基曾经偏执地认为,诗人转向散文写作,永远是一种衰退。但王族并不这么认为,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来回击着这种说法的荒谬。一直以来,他都是以诗歌、散文,并驾齐驱地在行走,而且还走得很稳,健步如飞。或许,正如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诗人的散文》里说的,诗人的散文不仅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种特别的题材:诗人的使命感的形式。这种使命感,在王族的这本书中到处都可以见到的。阅读的过程,也是越往后读,越觉得渐入佳境。
古人曾有写文章“妙不可言”、“不可妙言”的两难之说。但收入书中的诸多篇章,都是只宜看不宜说的。或许,对于作者或者许多读者,无论是妙不可言还是不可妙言,我如此絮叨,早已显得多余了。
《第一页》,王族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1年9月,16.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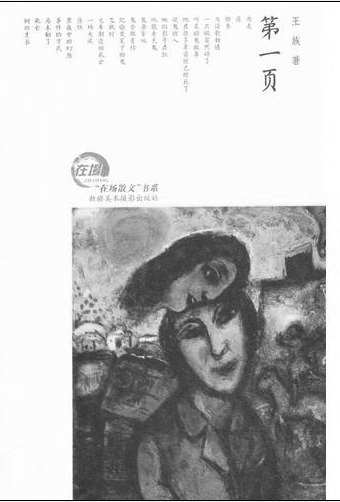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