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年来不断受到关注,出现了不下十种重排本甚至校注本。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便于获得的新版本,商务印书馆此番又何必多事,再出一种“新校本”?简单的回答是,此次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实系用校勘古籍的方法,汇集众多原始版本,来重新校订这部业已“正典化”的现代学术史名著,旨在为学术界、读书界提供一个较可凭信的版本。尤其是其所用底本与以往各种重排本均有不同,其版本选择的细节与用心,有必要在此稍作交待。
一、版本溯源
1923年9月起,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课后印发有讲义。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找到上书口题“清华学校讲义”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铅印本一册,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经过与张荫麟等听讲者回忆的对照,确定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原本(以下简称“讲义本”)。
此外,该讲义的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亦曾在报刊上先行发表,计有:
1、《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原载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内容相当于单行本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2、《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原载1924年3月2日至6日《晨报副镌》,即单行本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部分。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载1924年4月(实则7月以后)至1925年10月(实则11月以后)《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第3-8期。包含单行本第一至十二讲全部内容;经比对,即为前述“清华学校讲义”的转载本。
4、《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原载1924年6月至9月《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13、15-18号,相当于单行本第十三至十五讲(此本以下简称“杂志本”)。
至于梁启超此书的单行本,最早者为上海民志书店在1926年7月初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1929年10月已发行至四版(以下简称“民志本”)。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合集》,则在“专集”部分收入该书(以下简称“合集本”)。
上述诸本当中,“合集本”无疑为此后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被翻印多次,198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重排本,基本上都以“合集本”为底本。朱维铮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虽然也提到了“民志本”(校注引言误民志书店为“民智书局”)与“杂志本”,但从该校注沿袭部分“杂志本”无误而“合集本”转误的地方可以看出,其主要依据的应仍是“合集本”。因此,评估流传甚广的“合集本”之优劣,就成为说明新校本必要性的关键。
二、“合集本”之不足
1930年代由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据说是“据初印旧本覆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定”,“专著各种”更经陈寅恪、杨树达等参与厘定(《饮冰室合集·例言》),长期以来为文史研究者案头所必备,似乎是可以凭信的善本。但由于这套书结集较早、出版仓促,在专业研究者看来,却“存在着遗漏甚多、校勘不精的毛病”。(参见夏晓虹《结缘梁启超》,载《十月》1999年第3期)
不仅如此,《合集》体例设计的一大缺陷,是将梁启超许多原稿、原刊本所用的新式标点,一律改回了旧式断句点,并取消很多书稿当中用空行、连续星号等标记的段落区隔。众所周知,梁氏文字以“笔锋常带情感”著称,五四以后撰著多采用新式标点,尤其多用叹号、问号、省略号等。这些符号背后所饱含的“情感”,却被《合集》貌似庄严的体例抹煞了。
这些《合集》本子的通病,在收入“专集第十七”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里当然未能幸免。以校勘失审而言,“合集本”固然不像此前“民志本”那样错讹满眼,但其沿袭甚至新增的错误仍不少。如第十一讲罗列梅文鼎所著历算书,合集本自《仰观覆矩》以下20种数学书,竟都归在“测算器及其图说”一类,而紧接着另列“算学之部”,却只有区区4种书,令人生疑(见合集本第145-146页);实则若对照讲义原本,则不难发现实是“算学之部”一行与“仰观覆矩”一行倒置,而此前的20种书均在“算学之部”内。又如第十三讲所附《郑、顾、江、段古韵分部比较表》,所列韵目字多有错排(第216-217页);后文梁启超用“英文拼音”拼写陈澧四十音类,合集本所印字母亦大多错误(第222页)。这些讹误在最初的“讲义本”、“杂志本”中都是没有的,而新出各种校注本、重排本,却往往因为采用“合集本”为底本而未能全部改正。
更为严重的是,“合集本”似乎未能依据梁启超的原稿,而是选择了错误最多的上海民志书店版作为工作底本。这一点,可以通过民志、合集二本错误相沿的事实得到证明。“合集本”第190页第7行有下面一段文字(这里保留合集本所用的断句点“·”):
试总评清代·学之成绩·就专精解释的著作论仪·算是最大的成功
不难看出,此处原句应为:“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精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合集本在第一、第三两个断句点的位置,漏掉了两个“礼”二字。这样的脱文是怎样造成的呢?试看“民志本”第306页倒数第1行,便可释然(保留民志本所用标点):
试总评清代○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算是最大的成功
民志本此处的两个“礼”字都用近似句号的小圈(○)来表示,大概是手民未能识别原稿而留下的标记,印刷时未及换去。但《饮冰室合集》的编校者却将这两个小圈误认为句号,并且在新版本中转换成断句点,平白地夺去了两个字的位置。与此类似的例子,尚不止一处,说明了从“民志本”到“合集本”的版本传承关系。
当然,“合集本”在照搬“民志本”错误的同时,也继承了民志本对早期版本部分错误的校改;同时,也有一些讲义、杂志、民志本均误的情形,最后在合集本当中得到改正。令人稍感费解的是,亦存在个别“民志本”不误,而“合集本”与初刊本同误的例子(见商务版第271页,第十三讲校勘记三十二)。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极少见的情形,而且是用字形近致误,未必来自版本承递。根据“合集本”对“民志本”大量雷同,似乎可以推测,“合集本”所用的工作底本,可能是在“民志本”原书上直接批改的本子。这个批改本补充、改动了一些内容,却仍保留了民志书店初版的多数错误。
三、更贴近原初的现场
校勘所用底本,究竟应该取“善本”还是取“定本”?这是校勘学上值得讨论的问题。“合集本”讹误较多,并非校勘意义上的“善本”。但与此同时,“合集本”作为最晚出的版本,其对原刊本的多处修改,如人物生卒年的考定,个别段落的增改等,又的确体现了梁启超学力、观点的进境,是否可以依此认为“定本”?比如在第二讲“讲义本”与“民志本”当中,关于章太炎的叙述是“是浙东人,受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类似的错误也见于《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节,实际上为了迁就所谓“浙东学派”的论述,将籍贯浙西馀杭的章氏,硬说成是“浙东人”。而在“合集本”当中,这一句改作“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便精确了很多(参见商务新校本第51页,第四讲校勘记六)。
然而,类似的内容改动占全书比例很小,而“合集本”究竟能否称为“定本”,实在值得怀疑。在讲义等原本当中时时出现、表示存疑或待改的问号(?),在“合集本”中仍有不少;人物生卒年亦仍有未能考定之处;第十五讲虽然补充了“地理学”一节,但第十一讲标题下的“陈资斋”并未删去,虽然事实上第十一讲没有一个字提到陈伦炯(资斋)。梁启超一生多未竟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不例外,不仅关于戴震、章学诚等人物的重要章节均告阙如,即便已在《东方杂志》预告的“金石学”、“佛学”、“政书”、“类书”、“丛书”、“笔记及文集”等部分,亦未克完成。所以“合集本”本身似仍不足以充当“定本”。
与其去追求一个错漏较多、进退失据的半成品“定本”,不如依靠“讲义本”、“杂志本”等较早版本,以求贴近梁启超当年在清华等校讲授的原貌。这是本次商务“新校本”编订的基本思路。若探讨“近三百年学术”本身,固然要去追求一个完整可靠的“定本”,但学术史研究往往后出转精,梁氏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即便有“定本”流传,恐怕亦未必能称完善。然而,如果我们调转目光,着眼于梁启超本人,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处在1920年代的“整理国故”、“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等潮流当中的思想文本,关注现代学者对“近三百年”的解读与发挥,那么梁氏学术史课程的意义当胜于撰述,“讲义”现场的真实性,亦比史著本身的完整性更为可贵。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本次校订采用了最接近课程原初状态的“讲义本”和“杂志本”为底本。“讲义本”目前只存前十二讲,较之后半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文体采用新式白话,更有课堂教授的现场感。后四讲则依据梁启超亲自寄予《东方杂志》刊载的本子,实亦是本自讲义底本,惟在文体上更近著述。二者拼合,再补充以“民志”、“合集”等单行本后来加以调整的内容,即成一完整而较为接近梁启超授课思路的新版本。
“讲义本”、“杂志本”虽然最早出,但较之后出单行本,如前所述反而较少讹误,堪称较善之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发掘,一些课程讲授时的原始状态,或者也能得到部分呈现。比如第一讲开宗明义,梁启超自报课程名称,讲义本原作“近三百年学术概略”,《史地学报》本亦然;至出版单行本时,方才改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参见商务新校本第11-12页,第一讲校勘记二)。此外,原讲义本及杂志本均用连续星号表示分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梁启超设计的授课段落;这些星号在“合集本”当中被删去,使得全书眉目不清,部分章节甚至显得冗长。而在新校本当中,亦尽量将这些符号及全部新式标点加以恢复,以力求还原梁氏讲义所传达的“现场”。
此次商务重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由多年来耕耘于梁启超研究领域的夏晓虹教授主持。该本的问世,亦与夏教授此前校订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一起,构成一个梁启超学术史著述的新校本系列,期待能为读者走近梁启超、融入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脉络,提供更为便利而可靠的途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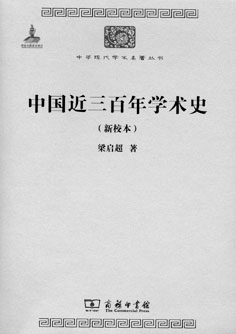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