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先生生前出版的理论性著作只有两本,即《美学散步》和《艺境》。而《美学散步》的全部文字也都收入《艺境》之中,故《艺境》应是宗白华先生生前出版最完备之理论著作。而从《宗白华全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一个旁及古今中外、糅合文史哲,试图沟连艺术、宗教甚至科学的体大思深的体系,《艺境》只不过是宗白华思想的冰山一角。
《艺境》的第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美。
鲍照曾说谢灵运的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而颜延之的诗是“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宗白华说:“这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他认为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绘画、工艺美术等中国古代艺术的各个方面。像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诗中的对句、园林中的对联等,都是一种“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美,讲究华丽和雕饰。这种美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但向来被认为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像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即“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比较起来,他认为“初发芙蓉”的美比“错彩镂金”的美具有更高的境界。
从历史的发展来说,真正崇尚这种“初发芙蓉”的审美理想是魏晋以后。宗白华认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到了宋代,苏东坡用奔流的泉水来比喻诗文,要求诗文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以至于人格美的理想,玉的美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苏轼又说:“无穷出清新。”“清新”与“清真”也是同样的境界,即“初发芙蓉”的境界。总而言之,魏晋以后这种“初发芙蓉”的审美理想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渐渐成为艺术创造中的正宗和主潮。
宗白华认为,这种“出水芙蓉”的美的理想在《易经》贲卦中就有它的思想根源。在贲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白贲”的含义。“白贲”就是“本色”、“无色”。宗白华说:“我们在前面讲到过两种美感、两种美的理想:华丽繁富的美和平淡素净的美。贲卦中也包含了这两种美的对立。‘上九,白贲,无咎。’贲本来是斑纹华采,绚烂的美。白贲,则是绚烂又复归于平淡。”白贲的这种自然、朴素的美就是最高的美,白贲的艺术境界因此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宗白华的这一思想,揭示了中国艺术的一种内在精神、气质和理念,把握到了中国艺术的内在血脉和律动,打通了我们与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心灵和情感的交感互应,为我们理解和领悟中国艺术提供了直达本质的最直观的路径。
《艺境》的第二个突出贡献在于:阐发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意识和观念。
建筑是视觉感受最直观、最强烈的艺术。在宗白华看来,中西建筑之间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在对空间的使用上:古希腊建筑“内部与外部不通透。祀者在庙外空场上。罗马万神庙,只由(有)顶光。中国则每室自凿窗户,内外通光,后又可加回廊围绕,故全部显得玲珑剔透。廊,檐,栏等,加强此印象。”这里的“通”、“透”与“不通”、“不透”有着根本的区别,表现着美感的民族特点。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周的自然风景没有在意,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中国人不同,比如“我们看天坛的那个祭天的台,这个台面对着的不是屋顶,而是一片虚空的天穹,也就是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这是和西方很不相同的。”这样,园林艺术在中国几乎与建筑是不可分的。中国的园林采用借景、分景、隔景等手段来创造、扩大空间,创造艺术的意境。因此,“不但走廊、窗子,而且一切楼、台、亭、阁,都是为了‘望’,都是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即达到所谓“山川俯绣户,日月近雕梁”的意境。此外,中国戏剧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布景(仅用少量道具),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让空间展示出来,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
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在绘画中则更突出地体现出来。西方油画是在二维的平面上力图表现出一个三维的空间世界来。而中国古代画家是运用“三远”(即宋朝画家郭熙所说的“高远”、“深远”、“平远”)的方法对外在事物进行描绘,画家的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由高转深,由深转近,再横向于平远,成了一个节奏化的行动。”因此,中国画法不重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意境。虽然它的出发点也极重写实,如花鸟画写生的精妙为世界第一。这就造成西方绘画在境界的层面与中国画描绘超实相的抽象笔墨结构有着天壤之别。西洋人曾说中国画是反透视的,其实在中国人看来,从固定角度用透视法构成的西方油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这样,中国画就展现出一种与西洋油画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如果说,西洋油画境界是光影的气韵包围着立体雕像的核心,那么,中国画的光是动荡着全幅画面的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的流行,贯彻中边,往复上下。所以,虚白就成为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宋代画家马远就因常常只画一个角落而得名“马一角”,剩下的空白并不填实,却并不感到空。清代八大山人画一条生动的鱼在纸上,别无一物,令人感到满幅是水。齐白石画一枯枝横出,站立一鸟,别无所有,宗白华认为其“用笔的神妙,令人感到环绕这鸟是一无垠的空间,和天际群星相接应,真是一片‘神境’”。
这些小中见大,有中见无,化虚为实,都是中国艺术的共同特征。它不仅在于通过艺术手段对客观外界化虚为实,更在于艺术家和欣赏者心中空寂的诗心,即“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心灵和心境:“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趣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意境’。”
意境就是诗和画、情和景的圆满结合,即时间和空间的交汇。所谓画中有诗就是在画面的空间里引进时间的感觉。诗中有画则是在诗歌流动的时间中展示了一个个具有空间感的画面。构成中国艺术意境的这种时间和空间感,归根结底来自于中国哲学中的道。所有中国艺术中的虚空和空白,“不是几何学的空间间架,死的空间,所谓顽空,而是创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着的道”。因此,对于中国艺术的体验,同样也是一种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道这种流动的精气、神韵,最生动地体现在中国“舞”的创化过程中:“‘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
道是中国人独特宇宙观的展示。宗白华说:在中国哲学中,“老、庄认为虚比真实更真实,是一切真实的原因,没有虚空存在,万物就不能生长,就没有生命的活跃。儒家思想则从实出发,如孔子讲‘文质彬彬’,一方面内部结构好,一方面外部表现好。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但是孔、孟也并不停留于实,而是要从实到虚,发展到神妙的意境:‘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就是虚:只能体会,只能欣赏,不能解说,不能摹仿,谓之神。所以孟子与老、庄并不矛盾。他们都认为宇宙是虚与实的结合,也就是《易经》上的阴阳结合。”这种虚实结合的宇宙观,总起来说就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
因此,“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象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象那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甬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由此可见,中西艺术技法的差异,比如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甚至水墨和油彩,线条和颜色,实质上是表现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宇宙观。
宗白华的美学是与他对于中国形上学的思考联成一体、互为表里的。从上述这些极精微的思想和方法中不难看到:叔本华、柏格森以及康德对于本体、生命和时空的理论,构成了宗白华思考的一维;他把这些理论与《易传》、老庄以及禅宗等思想融会贯通,从具体的作品体悟入手,揭示了中国艺术美的理想,破解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之谜,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精湛、绝妙的思想。他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不仅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都应该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和意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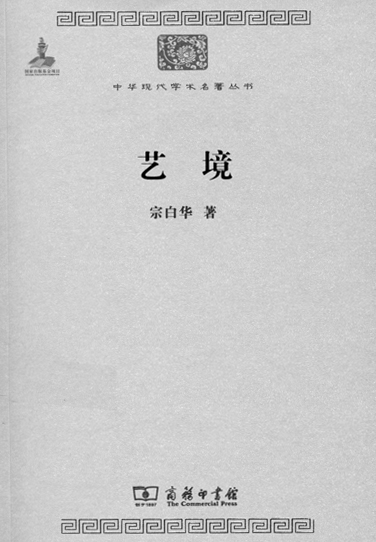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