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和评价
1994年,顾彬(Wolfgang Kubin)在瑞士的联合出版社(Unionsverlag)出版了他编译的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这是德语世界首次如此大规模地从中文原文翻译鲁迅的著作。顾彬在“序言”中指出:“每一个译本都是对原著的一种阐释,并与译者本人的理解及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他对以往的德文译本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指出这些译本漏掉了一些看似无足轻重但却非常重要的字眼:例如《呐喊》“自序”中的第一句话:“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不论是卡尔莫(Joseph Kalmer,1898—1959),还是霍茨菲尔德(Johanna Herzfeldt,1886—1977),抑或是杨宪益的英文译本,都没有将这个小品词“也”翻译出来。而这个“也”字不仅表现出了过去与现在时间上的转换,同时也表达了处于热情和失望矛盾之中的叙事者的内心。从这个翻译的细节,可以看出顾彬对鲁迅作品理解的深入程度。
顾彬认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就其形式的严谨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能够与作者(指鲁迅——引者注)匹敌。相似的情形只有在国际语境中才能找到。”一直到最近,他依然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代表着“中国的声音”。他在译后记中写到:“思索的勇气和自嘲的能力事实上使鲁迅不仅成为了现代中国最富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家,这一特征的影响直到语言运用的层面之上都能看得到……”
顾彬对杨宪益夫妇的鲁迅译本很不以为然:“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摆在他们眼前的是杨宪益夫妇的还是约翰纳·霍茨菲尔德漏洞百出的版本。”他之所以重组人马再次翻译鲁迅的作品,是因为他对以往的译本实在不满意。对像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1944)这样的作家只能从英译本转译部分作品的做法,他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而对上文提到的卡尔莫,顾彬的评价是:“他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包含着粗浅的理解而行文不畅的版本而已;繁杂的语句被改写或是被删除掉了。无论是原文的优美还是它的思想深度都不能从阅读中得到体察。”顾彬进而对这类充斥着大量错误的翻译表示了他的怀疑态度:“在难于理解但对解释来说显得举足轻重的段落里出现的大量细微错误常常使翻译的可靠性受到彻底的怀疑”。
顾彬在翻译鲁迅的过程中,尽管认为当时大陆官方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四版,1981)的注释可供参考,但同时也表示出了他的批判性态度:“它们(指注释——引者注)常常是意识形态化的,离题太远而重复冗赘。”更让顾彬不理解的是,这个版本省略了很多的内容:“许许多多的引文和影射没有给出注释,或许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或许由于相关的文献还没有公之于众。”正因为如此,顾彬同时使用了日文评注版的《鲁迅全集》(东京,自1976年开始出版)。
针对中国大陆对鲁迅的盛赞,以及海外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贬低,顾彬的观点是:“既反对视鲁迅为纯粹革命的正统观点,也反对将鲁迅看作虚无主义者的反教条主义观点,我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理解。时代精神的批判性分析无疑是贯穿鲁迅作品始终的一条红线,而长久地坚持独立性也使作家付出了代价:寂寞、厌烦或者说是无聊和苦闷。”对于中国来讲,顾彬认为鲁迅的意义在于创造了文学的语言,而对于西方来讲,则在于摆脱了服从精神:“马奈·斯珀波通过其写作所要求的那种对乌托邦终会破灭的毫无保留、不加粉饰的洞见,似乎在作为作家和人的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中得到了试验。”
顾彬善于捕捉到中西诗学的异处,他同样善于将中国文学特殊的审美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展现在德国的读者面前。在鲁迅那里,这一独特的写作方式有时并非中西的差异,而更多是传统与现代的不同:“面对不再是确定的、也不能确定的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复杂问题,现代作家采取了一种写作形式,他不主张终极而主张暂时的东西,不存在‘叙述的过程’,而形象与情绪与感觉的自由无穷无尽状态。世界成了幻想的材料和表演场,语言开始从陈述中解放出来。”
《彷徨》以及其他的作品所展示给读者的是,清醒之后并没有出路,这是鲁迅一再告诫现代人的窘境。顾彬之所以喜爱中国现代文学,与这些文学家们所揭示的现代性有关。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作家
顾彬认为,1911年,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帝国的解体,以及在此之前的科举制度之废除,导致了中国人“整体性的丧失”,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的内在基础。现代性便是由于整体性的终结而产生的:“生活的内在意义”瓦解了,人变成了一个寻觅者和一个流浪者。人们为失去了传统而绝望,并且传统的资源已经无法提供解决个体“忧郁”的任何解决办法了。因为在人与上帝的分离中,在其先验性的无家可归中,人认识到他自己和他的整个存在都成问题的。这是顾彬借用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的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界定。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家有关“忧郁”和“苦闷”的相关研究,可以说都是在追问他们和现代性的关系,而这绝不仅仅局限在东亚一隅:那个时候中国的确有一个很好的现代性文学,这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没办法比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批至今未被关注的作品,通过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它们‘关键文本’的价值。这些作品,不仅在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且在对20世纪人类心灵的理解中具有关键作用。”
顾彬认为,现代人存在的碎片化在鲁迅的第二部小说《彷徨》(1924—1926)中“得到了犀利而深刻的描绘”。“这部小说集展示的是这样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他欲前行,但不知道要去何方,因为在任何地方他都不再有终极归宿。”顾彬同样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1928)中看到了一个处于持续变动的世界中的现代人的状态。而这不论是夏志清,还是普实克(Jaroslav Pr šek,1906—1980)抑或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都没有真正认识到的。
顾彬认为,通过中国现代作家我们可以了解20世纪文学发展的所有问题,亦即上帝死了之后人该怎么办的问题。不论是郭沫若在《天狗》中以“我是”的句式表现出的自我主体,还是鲁迅在《彷徨》和《野草》中描写的在路上追求理想的人,这些绝不仅仅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同样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悲剧。因此顾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代表着20世纪的中国,也代表着这一时代的欧洲,是具有世界代表性的。
当代文学与市场
如今顾彬尽管可谓名声大噪,但他依然保持着书生本色,显得与当今的社会是那么格格不入。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跟他作为一个崇尚高雅品位的唯美主义者有关。举例来讲,尽管他在波鸿大学跟随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学习过多年的汉学,但他依然无法容忍这座大学和所在城市的平庸风格。他曾在伯尔尼的一次演讲中,非常委婉地说了他“对这所大学及所在城市的建筑充满了困惑和不解”。
他在大学跟霍福民所学的是唐代的诗歌和宋代的散文,正是由于他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情有独钟,致使他用中古和近代的文学审美来看待当代的文学成就,这其中的断裂是必然的。他认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曾经走过这样的歧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描述的也是一段步入歧途的历史,而这是东西方现代性的产物。”
去年12月4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驻京评论员西蒙(Mark Siemons)对顾彬与杨锐在中央九套英语对谈的报道和评论,顾彬对文学的市场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而走向市场经济后,由于市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很多人便天真地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而没有看到“市场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实际上,正是这所谓的市场经济社会破坏了文化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毁掉了人类的伦理道德。随着语言的商业化,知识分子也逐渐消失于公共空间的舞台上,这当然不仅仅在中国,只不过在中国表现得更明显而已。顾彬不能容忍的是,中国作家变成了这些消遣文化的参与者,“将自己那灰暗的躯体作为献祭的牺牲”。这导致作家的批判精神渐遭抛弃。因此,顾彬祈盼发自当代作家心声的中国的声音。
有关当代文学的市场化、商业化,李公明也指出:“最大的问题是一些中国作家缺乏意志力,不能为他们的艺术忍受磨难,而是为商业世界服务。这里可以看出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忧虑:商业化销蚀了文学的灵魂和规范。”令顾彬稍微感安慰的是,中国的很多诗人没有太多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得到市场的推崇,他们依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所以不会出卖自己,还会专注于语言和艺术的价值。
顾彬认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他发现,作为犹太人的葛浩文删去了《狼图腾》的最后一部分,因为从政治正确上来讲,这一部分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因为他(指葛浩文——引者注)决定了该书的英文版应该怎么样,他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立场。”
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某些作家的痛斥,对文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非难,我以为都说到了痛处。鲁迅晚年曾引用郑板桥(1693—1765)的两句诗赠给准备为他写传的增田涉:“抓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想这也正是顾彬为很多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最主要的原因吧,因为他犀利的言论似乎触动了某些国人的敏感神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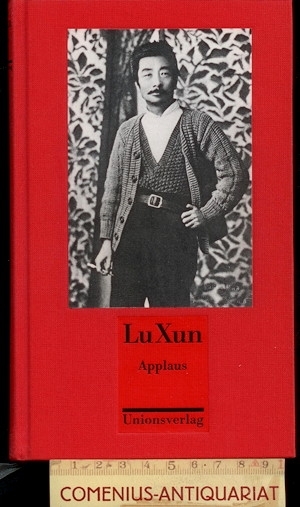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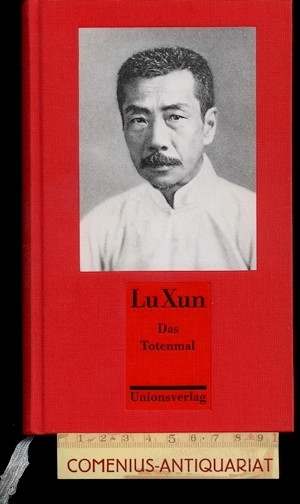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