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集》(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一书由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分会出版。研读这部整整80年前由中国人编写、在上海出版的英文著作,不仅为我们考察民国时期的出版史和学术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新视角,而且可以知道,中国文化原来是可以这样介绍给外国读者的。
这部英文著作介绍了中国工业、农业、地质、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既有古代的历史,也有近代的发展,内容十分丰富,作者阵容异常豪华:丁文江、胡适、蔡元培、赵元任、任鸿隽、李济等多位知名学者都在该书中有所贡献。这些作者除蔡元培外,皆有留学英美的背景,不仅专业强,英文也好。蔡元培的一章(《绘画与书法》)由林语堂负责翻译,文情俱美。
这本英文论文集的读者对象无疑是西方人。当时一般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存在不少偏见。针对他们的固陋,该书的作者们在正面论述中国文化的同时,也给予这些偏见以有力批评。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一章中指出:“据说中国人在文明民族中是最不信宗教的,中国哲学最不受宗教影响的支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以上这两种评论并非符合实际。历史研究将使我们确信,中国人能够具有高尚的宗教感情。”丁文江在简要考察了中国文明史后,在结论部分写道:“中国文明是4000年以来文化努力累积的产物,其生长是缓慢的,且不止一次被打断,但她从来没有丧失其生命力,而且从总体上说,比其他地方譬如说近代欧洲的进化,更具连续性。此外,虽然中国大多数时间里都与比自己优秀或与自己平等的文化相互隔绝,但是,一旦能够保证足够长时间的直接接触,她会尽取外国文化中值得学习的优秀成分,而且一旦学到手之后,她总会在这些新的文化成分之上打上自己创造力的烙印。”这些论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中国文化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呢?当然不是,这些在英美留学多年的精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在国内他们可以激烈地批判中国文化,但是在面对外国读者时则不约而同地为之辩护。
说到这本书的由来,必须提到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这一学术组织建立于1925年,最初是由夏威夷关心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发起的区域性团体,其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求改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后来学会经过扩充,吸收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并且得到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总部迁至纽约,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均设有分会。在1960年由于麦卡锡运动的冲击而解散之前,太平洋关系学会资助出版了大量有关亚洲的书籍,为填补西方国家对于太平洋地区知识的缺陷,作出了其他任何学术团体都无法比拟的贡献。
中国分会在出版方面也配合总会做了不少工作,其出版物除《中国文化论集》外,还有二十余种,如陈启天《192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规划与重建》(Chinese Government Economic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since 1927,1933)、刘大钧《上海的发展与工业化》(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 , 1936)等等。这些英文著作现在都不易见到,建议有眼光的出版社予以影印再版,如能翻译成中文出版,尤为嘉惠学林的盛事。《中国文化论集》已经有了中文版(王宪明、高继美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给收藏、阅读和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陈衡哲是太平洋关系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曾连续四次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该会每两年一次的年会。编印《中国文化论集》的想法形成于1929年的京都会议,这次会议 “会期共十一天,却有三天用来讨论文化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时间安排。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资料极少,涉及中国文化时尤其如此。中国代表团的同事深感欲使1931年的讨论会更有效,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工作。结果大家决定编一本《中国文化论集》,而这一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偶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编者前言》)陈衡哲不仅承担了全书的编辑工作,还撰写了《结论》一章,指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尽快实现现代化,同时也充满乐观地预言:“中国不仅能够‘取’,同时也能够‘予’。历史证明,在工业和艺术方面,欧美国家早已从中国的发明之中获益,时间将会证明,中国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出更重要的贡献。”这是民国学人的期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期望。
1931年会议的东道主是中国,这应当是陈衡哲组织编写《中国文化论集》的又一大动力,她希望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加深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当时不要说是一般西方民众,就是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了解都十分有限。这当然是由于教育的缺失。以美国为例,虽然早在1877年耶鲁大学就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标志汉语和中国研究正式进入了美国大学体系,但此后的发展十分缓慢。耶鲁第三任汉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大学给予中国研究的关注很少,在给予某种程度关注的大约三十所大学中,中国仅仅是在一个学期关于东亚的概论性课程中被涉及,只有在三所大学中有能够称得上对于中国语言、体制、历史进行研究的课程。美国的汉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这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必须到欧洲去寻找教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美国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29年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19年建立的全国性学术促进机构)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希望以此来改变美国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大大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局面。为了配合1931年的中国会议,“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专门指派人员,对委员会成立两年来美国大学在有关中国研究的课程设置、图书资料、学术梯队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调研,其调研报告于5月份出炉,题为《美国之中国研究的新进展》(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些新进展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中国学者们明白,虽然中国早晚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但其主导权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931年正值多事之秋,会议地点原定北京,后改为杭州。“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原定10月21日开始的会议更面临延期甚至流产的危险。9月25日,陈衡哲和在北京的其他中国代表以及先期到达的美国代表共进午餐,商讨会议的前景,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应该如期举行。这一建议随即以电报的形式传达给已经到达上海的代表:“本次会议是表述中国立场的好机会,但作为东道主这么做有相当难度。建议理事会尽早开会决定。如决定举行会议,务必保证外国代表安全和中国代表出席。”(原为英文,据胡适当天日记翻译)在中国代表的多方努力下,会议终于如期召开,地点则再次改为上海,会议日程也做了一些调整。代表中国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陈衡哲,还有颜惠庆、陶孟和、丁文江、胡适等人。
陈衡哲是民国时期的才女。她于1914年通过清华留美考试,成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的女生;她在美国专攻西洋史。1920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是北大最早的女教授。陈衡哲在留美期间与不少中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特别是和胡适互相倾慕,但由于胡适有母命在身,有情人难成眷属。陈衡哲后来嫁给了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康乃尔大学时的同窗好友任鸿隽(叔永)。任专攻化学,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在《中国文化论集》中,《科学的引进及其发展》一章理所当然地由任承担。胡适除承担《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一章外,还写了《文学》一章,介绍近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论集》中,都是一人一章,胡适是唯一一人写两章的,除了他在民国学术界的显赫地位外,他和陈衡哲非同寻常的关系大约也是原因之一吧。
《中国文化论集》的近二十位作者不仅在学界声誉卓著,好几位还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如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部总长等职,朱经农曾任教育次长,翁文灏后来更是做到了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与众多的男性大腕相比,陈衡哲和另一位女性作者曾宝荪(曾国藩玄孙女、教育家)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但女学者毕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抢占”了主编的位置。民国学术的繁荣在今天仍然被津津乐道,其背后的原因很值得深思,从《中国文化论集》这本书来看,女性学者的崛起以及不讲什么论资排辈的风气,也许可以算是其中的两条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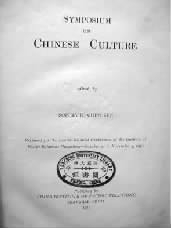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