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整日为现实奔忙的人而言,“武林”这个概念大多只存在于诸如金庸小说和徐克电影里,遥远而古典,带着超现实的玄妙。谁曾试过穿行街巷或漫步公园时迎头遇上个把大隐于市的武林高手呢?除非具有作家徐皓峰那样的眼力。在新作《大成若缺:八十年代习武记》序言里,曾有过习武经历的他道出此书的诞生正是源于其2003年某个冬日于河边散步时邂逅大成拳传人王建中。书中内容来自王建中的口述回忆,经济复苏、思想飞扬的八十年代也是民间练武风气斐然的时代,那时“武林”有说不尽的兴衰起伏、恩怨情仇,那些往事经徐皓峰之手记录下来,热闹之外更有对处世哲学的参悟与社会景况的侧面旁观。
从口碑上佳的口述回忆《逝去的武林》到小说《道士下山》、《国术馆》,再到去年末的长篇小说《大日坛城》,纪实也好虚构也罢,徐皓峰的写作或多或少与武林、武学相关。写作之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出身的他似是无师自通,他的作品文学性强,感情克制,词句严谨,时有宗教、哲学意味氤氲其间。写作之外,编剧本、研究道家文化乃至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做电影导演都让他乐此不疲且颇有心得。
前段时间进行新片后期制作的徐皓峰一度忙到晨昏颠倒,令这个采访一约再约。在他常去的一家咖啡馆,他轻车熟路带我到二楼找个安静角落的半开放式空间坐下。相貌斯文敦厚的他看上去没什么外露的侠气,说话慢悠悠的,气定神闲成竹在胸的自信。偶尔迸发的笑声几乎有点卡通般的憨,附带的手势比表情丰富。说到参与王家卫新片《一代宗师·叶问》的编剧工作,他一笑包含言语难尽。谈及他最近自编自导的电影《倭寇的踪迹》,他滔滔不绝起来。在我写这篇采访稿的时候,从意大利传来消息,此片已入围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
读书报:曾经习武、研究道家文化,写小说与整理口述历史、电影编剧并行不悖,在北影当老师,最近自己做导演,你的身份太多元化啦,这些对你的精力会是一种分散吧?
徐皓峰:以前不会,以后会。人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刚开始的阶段,比如大学毕业头十年肯定是要多方面涉猎,虽然我写了很多东西,但那个阶段基本是吸收养料、认识社会。男的过了四十要把爱好和特长专注在一到两个,一个人同时追两只兔子一定搞砸。我以后主要是写小说和做电影导演,如果有了写口述历史的机缘,我也不会排斥,对我来说那是顺手牵羊,成果是别人的。
读书报:想了解大成拳却无处入手,后来在河边邂逅大成拳撑旗人王建中,不止了解大成拳更以其口述内容写出《大成若缺》,这种写作机缘实在是非常戏剧性。
徐皓峰: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心想事成,这辈子没有成的下辈子一定会成,会被你的心念招来。我的世界观,一方面是心想事成,一方面是无常。你肯定会招来缘分,但这缘分有多久,以何种方式收场,是无常的。
读书报:《大成若缺》中的很多人物令人过目难忘,武林中人如此,连那个给王建中画像的八一湖流浪汉老周也很富传奇色彩,平日里你是否特别留意这类人物?
徐皓峰:是的,我从初中开始就经常在公园、小树林、河边逛,那里常有些社会边缘人,甚至精神有问题的人。老周非常神,我在书中用简练笔法写他的经历,你会觉得这个人传奇得不得了。当年我学大成拳的时候天天能看到老周,像他那么偏执的人,身上除了传奇,也会有邪气,还有天真的一面。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比如北京南城花鸟市场里面那些玩鸟的养鱼的撂跤的人,他们除了穿的衣服是现代的,其他方面简直和明朝清朝市井中的北京人一样。
读书报:你在《大成若缺》的序言中说,“英雄也是落魄了才好,英雄得志了,一定失控”,书中主人公王建中半生颠沛的经历似乎印证这一点?
徐皓峰:人生一定有缺憾,有些东西如果没有遗憾的话你也得不到。王建中如果在商场上一直像他开头那么顺利,现在可能他就是个先富起来的人,常年呆在夏威夷,精力消耗在享乐上,也不会在八一湖遇到我。老天会故意把你的一些东西拿走,逼着你去追求别的东西。
读书报:你在写作《大成若缺》过程中对王建中的讲述如何进行取舍?
徐皓峰:从口述到写作的处理主要是在武学上,有很多很好的影评乐评,但影评乐评和电影、音乐会是两码事,武术也是这样,真实的教武术和整理成文字也是两码事。很多时候取舍也挺可惜,王建中说的很多话习武的人根本听不懂,我在书中可能保留一两句以偏带全的、意向性的话。人回忆时总会把事情说得很周到,而周到就无趣了。我做口述历史的整理,最费劲的并不是怎么去挖掘,而是你如何找到合适的文学形式。
读书报:从创作者的角度,写小说和口述历史的整理,哪一个成就感更大?
徐皓峰:做口述历史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是我对某个学问最好的深入方式,小说创作是能量的释放,你得把自己沉淀的东西掏出来。倒不能说口述历史的意义更大,作家是需要营养的,写口述历史是对写小说最好的调节。
读书报:你说撰写口述历史是满足自己,写小说是另一个状态,你是个会考虑读者感受的作家吗?
徐皓峰:在知识上我是不考虑读者感受的,但在叙事上,就跟一个话剧演员一样,当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一定会对观众有个关照,叙事就是这样,肯定要顾及读者,不然就不成其为叙事。小说的叙事就跟一块牛排似的,有的六分熟,有的三分熟就够了,不需要读者全部吃透。
读书报:你的创作是预设主题然后动笔,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提炼出主题?
徐皓峰:一定是一边写一边才有主题。写小说和画画差不多,画家在创作一幅作品之前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全,开始有个意向,抓住了,真正的结构和主题都是在追逐意向时慢慢形成的。凭空思考得很周到的事情,写出来会发现特别没有意义。设想得体系完整的作品,真地动笔会发现其实以偏带全更好,写出一面就可以了。创作的乐趣就在于重新找到分寸感,凭空想象、设计终究还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而逻辑和分寸感实际上是两码事儿。
读书报:谈到分寸感,你的《大日坛城》中在对武学或棋道的描写上既克制又铺张,很多场景点到为止,但气氛渲染和想象空间又神乎其神,这种分寸感是你在写作过程中对自己的暗示?
徐皓峰:《大日坛城》不太像这个世纪的小说,如今很多小说开始散文化,大家更追求意境和抒情,小说通过情调来表现等于在干音乐的事情。读完杜拉斯的《情人》,你对法国人在越南殖民地的背景仍然不是特别了解,而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社会底层的描写,那是两个世纪前的小说传统,除了告诉你故事,还会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我很早以前就开始克制自己的小说语言,语言的克制反而给读者增加更多意境,我更想在小说中建立一套知识系统或者是叙事系统。
读书报:《大成若缺》也好《大日坛城》也罢,你的作品里总是将武学和哲学乃至宗教联系在一起?
徐皓峰:没有人教我写小说,我的文学阅读量也不大,我的写作才能来自于大学时的训练,我的文学是从这上面长出来的。叙事传统能够超越电影和文学两大创作门类,电影是叙事,小说也需要叙事,我受到的电影叙事训练,同样适用于写小说。我在一个故事里一定要体现价值观,没有价值观就没有故事,故事里最动人的一定是某种特殊价值观。我书里的传统文化因素,包括宗教、哲学的因素,其实都建立在价值观意义上,我感兴趣的是人可不可以以另外的思维方式活着。
读书报:有人认为《国术馆》的超现实意味很浓,刚才你也谈到马尔克斯,你是否对拉美文学有偏好?
徐皓峰:有一段时间对拉美文学是有偏好的,但我毕竟和莫言那些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不一样,他们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对我来说,极度夸张的拉美作品令我觉得跟自己的血统非常远。我在《国术馆》里已经对超现实的程度很克制了,以前写中篇小说的时候我有几篇是很魔幻现实主义的。其实,博尔赫斯对我的影响要比马尔克斯更大。
读书报:写作上有什么新计划吗?
徐皓峰: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希望今年十月份能写完。我不敢让写作中断,一旦断了再恢复是非常费劲的,有两年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不要让写作间隔超过一周,我如果有一周没有动笔,回头再写的时候,连语感都不对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由一个熬夜的作家变成一个清醒的作家,晚上十二点睡觉,大概早晨三四点起来写作。这个方法是跟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学的,他觉得这个作息写作效率最高。还有一个办法也很管用,我在今天早晨写作时一定不把文思都写出来,这样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写就能顺利开头了,每天留一点,哪怕句子和词都想好了,也不写完。如果今天我把灵感都用完了,第二天早晨坐那儿还得重新想,还得喝好几杯咖啡。
读书报:新长篇是写什么的?
徐皓峰: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写起,是写义和团的,反思中国拳脚如何应对洋枪洋炮。现在反对义和团的人很多,觉得他们体现了中国的愚昧,但是愚昧如义和团也有他们的操守。有的东西不能简单去看,是我们不了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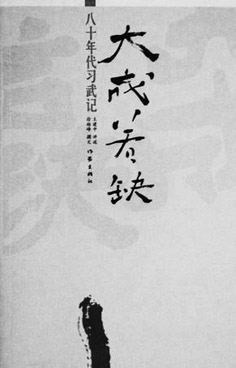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