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孙惠芬的心里,埋藏着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伴随她走过了漫长的黑暗之旅,终于在《秉德女人》中绽放开来。
她形容这次写作是一次黑暗中的写作。“所谓黑暗,是说我必须穿越跨度很长的历史,所谓探险,是说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惟一的光,是心灵,是贴近人物情感的心灵。”
她说,写作中,王尔德的诗一直萦绕耳畔:“我们都在沟中/可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天上的星空。”正是这首诗,激励她在黑暗里探寻,一寸一寸照亮乡村大地和在大地上挣扎的人们。如果说过去的作品是写女人心灵瞬间的历史,那么在《秉德女人》中,她努力书写的是在漫长的时间历史中女人身体的历史。她很早就有一个想法:写一个对身体敏感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因为只有对身体敏感的女人,她的情感维度才无限广阔,她的内心世界才无限丰富,她的命运深度才会在国家和政治变迁中无数次瑰丽绽放。
孙惠芬笔下的“秉德女人”出生在1905年的辽南海边小镇,一个尚未出嫁的美丽姑娘在看到世界地图后,开始幻想与丹麦传教士的儿子一起去航海看世界。她为了逃避跟父亲去教堂躲起来,却意外地被匪胡子掳走。经历与数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与子女的集合与离散,她倔犟地生根,养育果实,家族终于变得枝叶繁茂,她却在沉重的支撑和负重中渐渐老去。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孙惠芬:1982年,我在《海燕》杂志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那是一篇日记。我没上过大学,苦闷时天天记日记 ,我最初的创作,其实只为倾诉,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到1990年前后,才有了创作上的自觉。我的创作与我从乡村进城紧密相关。最初写作是为了逃离,书写的是对乡村世界的叛逆;后来的写作,是为了守望,书写的是对乡村土地的怀念和怀想。一直不变的是,在作品里,我努力揭示人性的困惑和迷惑,努力探寻人性的深度和命运的深度。
到2001年写《民工》和《歇马山庄的女人》,我才有了对城与乡的超然姿态。也就是说,十几年过去了,虽然笔下依然在书写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痛苦,但已经能够超越因个人奋斗而累加的复杂情感,能够更多地关注人物和当下现实的关系,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变革,以及社会变革带来的城乡之间纷繁而驳杂的深层关系。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2004年,我完成了《上塘书》的写作,有评论说我是在写地方志,其实那是一本精神志,是上塘的精神志。把村庄当成人来写,让村庄带着故事,一点点长出来,是因为乡村在我心里装载得太久了,积累了太多的情感,土地、街道、房屋、草垛,在长时间的怀想中拥有了灵性,它们也就变成人物向我走来,也就有了一桩又一桩精神事件。这一时期的写作,祥和而平静,就像坐飞机穿越乌云,在乌云之上,乌云变成了风景。可长期的平静,又让我有脱离地面的紧张感,于是2005年以后,我又开始调动各种欲望,就有了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吉宽的马车》的写作。
我写乡村,大地气息往往会扑面而来,写到城市,涉及城市灵魂的、本质的东西,就觉得虚弱,没有把握。
最后,我又回到乡村,回到大地,回到内心。
读书报:您很擅长写女人,这次写女人,和过去有何不同?
孙惠芬:这次写作与过去的不同在于,过去,无论是《歇马山庄》还是《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所写的故事只发生在一年里或者一个季节里,而这次却写了一个人漫长的一生。秉德女人生长在一个18世纪就与外面世界通港的海边小镇,她的一生,经历了国家和政治的无常风雨,在跌宕起伏的命运中,时间的跨度差不多是一个世纪,我跟踪她由年龄变化、身体变化而带来的心理变迁,在这个变迁中,大环境下的乡村虽然相对安静,战争也仿佛只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事情,可因为辽南乡村特殊的相对开放的地理位置,秉德女人很早就有了家国观念,很早就在不自觉中寻找生存的方向感。一些年来的经历让我懂得,对生存方向感的寻找,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城市乡村所有人群,属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这是一种存在感,它来自于生命的原动力。之所以要写敏感的女人,是因为只有敏感的女人才会忠诚于自己的身体,只有忠诚于自己身体的女人,她的心才是狂野的自由的,她由身体而抵达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更宏阔。这一点,是我过去小说里没有的。
读书报:秉德女人虽然只是个乡村女子,可读小说时感觉你在讲一个宏大故事,也可叫宏大叙事,人物和大时代瓜葛紧密,这和你从前的作品不大一样,是有意而为的吗?
孙惠芬:真就有读者说我在宏大叙事。我没有宏大的概念,写出这样一个故事跟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家族有关。我身后家族的背景里,就有基督教徒、匪胡子、国民党战犯、买卖人、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在我的家庭家族里,祖辈父辈一直都在追求和国家保持一致,他们野草一样生长在狭小的乡村世界,却一生都在企图和国家这根粗壮的血管相通,有朋友说这是中国人的政治归宿感,而我想表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就是前边说过的人的存在感。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读书报:为什么你对女人的心理和身体的把握,如此细致敏感?
孙惠芬:这得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在一个上有奶奶、父母、哥嫂、下有侄子侄女的四世同堂大家庭里度过,我的奶奶从封建社会过来,有着严格的封建家长作风,说一不二。母亲温顺贤惠,从不敢大声说话。我有三个哥哥,我三岁时,大哥就娶了大嫂,之后每隔两年娶一个嫂子。在既有奶奶、母亲,又有三个嫂子的大家庭里,我的童年备受压抑。我害怕奶奶的脸色,奶奶爱我,对我并不严厉,但她对母亲严厉,她的脸色常常要影响母亲的脸色;我害怕三个嫂子的脸色,在嫂子们眼里,我也只是个孩子,她们并不管我,可她们的脸色常常也要影响母亲的脸色。而我,每当母亲脸色不好,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一不好了,就格外留心奶奶和嫂子们的脸色。我的目光,从没有离开院子以外的世界,父亲在外面干什么,哥哥们在外面干什么,父亲和哥哥之外更远的外面是什么样子,从不关心。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跟随母亲,一会儿高山一会儿大海,没有一刻安宁。长此以往便培育了我的敏感和细致,也是因此我写不了麻木的女人。
当然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男人女人都能写,其实《民工》就是写男人的小说,《歇马山庄》也写了男人,只不过这部小说重头写女人。
读书报:您为此做了怎样的准备?
孙惠芬:阅读有关辽南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书,到故乡老街采访,之后长时间地在黑暗中发呆,去寻找更适合表现一个女人多侧面历史的小说形式。我原来是想通过她七个儿女不同角度的回忆来布局谋篇,这样可把时间打碎,可突破以时间脉络讲述故事的传统路数,可是临动笔时突然觉得那样容易拆散人物的骨骼,七个声道的叙述也容易造成混乱,另外,有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个写法也不再新鲜。某一天,以传统的写法写出两千字,一个女人已经在我的意识中复活,在女人狭窄的世界狭小的疆土复活,并一点点波澜壮阔,我的写作便开始了。
读书报:在写作上,您受到谁的影响更多一些?
孙惠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受萧红和沈从文的影响多。沈从文让我看到我身后的故乡是可以当成艺术来书写的,读到他的《湘西散记》,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身后的那片土地是我创作的源泉。萧红的《呼兰河传》让我百读不厌,她写荒芜的土地上忧伤的情感,童年自由的心灵,让我从此知道好的小说家更像大地上的野草,落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在任何时空里都能自由思想。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女人,您认为完美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孙惠芬:完美的女人,应该像地母般宽容,给男人以支撑。我觉得女人天然就该给男人以力量。秉德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大事情来临时女人是有力量的。在我心里,再优秀的男人也有孩子的一面,再不优秀的女人也有母亲的一面。
表面上看来,孙惠芬亲切随和,和她聊天,如沐春风。她却笑言自己“外圆内方”,想法不容易改变。体现在写作上,她从来不管发行量多大,也从没想改变自己,为市场迎合某些东西。她坚持为自己内心写作,固执而倔犟。
她的笔下,传达给读者太多的温暖。然而在她看来,温暖不是一味地写善,她说阳光照到阴暗的地方才叫温暖。如果忽视了人性阴暗的一面,只给人好的东西看,温暖是虚伪的,善也是伪善。她认为,作家真正的温暖体现在对人性的悲悯,对人性恶的、不美好的东西的理解和同情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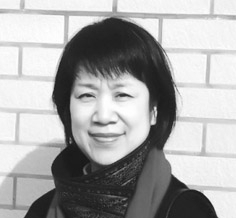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