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是当今仍然活跃的老一辈藏书家、散文家,著作等身,在读书界影响很大;为了庆祝他米寿,2006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曾举办了“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事后又将会上的发言和论文以及在此前后见诸报刊的有关文章编为一集《爱黄裳》(陈子善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该书可以说是第一本黄裳研究资料汇编;同类的文章,报刊上好像还有不少,所见且颇有异同,将来也许会再出新的研究资料汇编吧。
我还不能说是“黄迷”,他的大著是喜欢读的,凡曾入手者都曾一一认真读过,随手写过一点笔记,无非是些零星的记载、心得和感触。
一
人们吃过鸡蛋以后并不去关心下这个蛋的母鸡;而读过印象深刻的作品以后,却多半希望了解其作者。所以作家传记历来多有读者;“自述文丛”也因此大行其道,最了解该作家的还是他自己。
黄裳先生行将百岁,是当下健在的最老一辈名家之一,而且还不断推出新作,同若干伏枥的老骥相比,明显高出一头,他的经历自然为读者高度关注。由于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别人为他写的传(很应当有人动手),如此则《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为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自述文丛”之一)一书就太重要了。
这本书同“大象人物自述文丛”中各书一样,并不是传主的专门之作,而是从他过去的文章中摘取有关部分编排起来的,所以各个时段的详略往往很不均衡,也难免会有空档;但总归有一个大体,据此可以编出一份作者本人具体经历和精神发展的简谱来。我因为先前陆续读过黄老不少文章,所以对他的生平经历已经知道一个大概;而读过这本自述以后,知道得就更多更全一些,从而对他的文章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作者是著名藏书家,藏品在“文革”中的70年代初期被全部抄没。1980年所写的《书祭》一文中回首往事道:“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第195页);当时还由奉命前来的顾廷龙(起潜)等专家编过一份目录。后来的情形是:
直到一九八七年(按:当是一九七八年)的年末,我才又去拜访了顾起潜先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他告诉我,我的藏书中间的线装书部分,都很好地保存在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散失。同时因得到他的照顾,有些残破的书册还修补整装过,只要等政策确定,发布,立刻就可以发还。
此外,我还在另外的地方看到顾先生手制的我的藏书中间属于“二类书”的一份详目,并奉命照抄了三份。我还好奇地打听过,怎样的书才算“一类”呢?回答是并没有。我想,那大约是指宋版元抄之类的国宝吧。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第197页)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写过那么多古籍的题跋,也可以明白他那本《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版)一书的书影里,何以既有黄裳本人的藏书印,又有上海图书馆的藏书印,以及书的主人在序言中叹为“有如林教头脸上的金印,拂拭不去”!
失去的东西是特别可贵的。当作者复出,可以自由写作以后,首先发表的一批文章中以及后来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那么多是同他本人所藏之明清刻本古籍相关的篇什,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事了。
一位作家的写作路径,同他的经历永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所以非知人论世不可。文学研究中的传记研究法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尽管新派批评家很看不起这一方法,认为只是很不行的“外部研究”;殊不知舍外则无内,只读原文文本而不管其他,未免太可惜了。
《自述》图文并茂,印订甚佳,偶有误排和别种差错。例如上文所抄的一段弄错了年代,1980年写的文章怎么会提到1987年的事情?而且到七年后被查没的书已经发还了若干,作者虽仍然有气可叹,但已经不复完全“束手”什么事都干不成了——事实上80年代上中叶乃是他写作的高峰期,许多精品出现于此时。
又如本书中影印了一份张奚若的来信,而说明文字道是“冰心手迹”(第165页);有一幅照片是传主与两位友人的合影,说明文字道是“1990年与朱正(右一)等友人”(第220页),将其左一的姚以恩先生放在“等”字里,恐怕不够妥当。诸如此类,不必一一,虽属枝节,总是遗憾。此书再印时,建议彻底检查一遍,加以订补。
二
黄裳先生著作甚多,序跋也就不少。有些大著读者或一时尚未读到,先看一点序跋也是好的。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软性广告。
凡是书的序跋,最容易提到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感慨,历来是重要的传记资料。《黄裳自述》中收入序跋七则,即已足透此中消息。《黄裳序跋》(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7月版)录入序跋凡三十则,虽然尚非此类文章的全部,已足慰读者饥渴。
本书中多有图版,有些是各书初版的封面,与序跋对照着读,颇可增加兴味。另外还有不少作者的照片和有关的名家手迹,看看也很有兴趣,可惜比较杂乱一点,印得也不算很清楚,是一遗憾。对此作者本人是不大满意的,后来曾坦率地批评说:
前些时我印过一本《黄裳序跋》,编者自行删去了几篇较长的考订文字,腾出篇幅填上大量图片,相关和不相干的,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像大观园里的刘姥姥,经鸳鸯、凤姐打扮,插了满头花朵一样。刘姥姥心里明白这是捉弄她,但只能强颜欢笑地凑趣,共同演出这场闹剧,其处境、心情是可以理解,并予以同情的。我不是刘姥姥,只得坦率地说出我被打扮后的不舒服来。这是我与图文书的第一场失败了的遭遇战。(《二十年后再说“珠还”——写在新版〈珠还记幸〉重印之前》,《珠还记幸(修订本)》卷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
黄老作为口味考究的藏书家,非常看重版刻之美,他的不满是可以理解,并予以同情的。图文书要想出得好,固然首先要精心编排,合理布局,同时也得纸墨精良,不惜工本——如此则投入必然增加,书价也必高,而这样一来又难免会影响销路。一般的出版社底气本来就不大足,最怕的一件事则是赔本,实处于两难之境,这也是需要予以体谅和同情的。
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出图文书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把好事给做砸了。
三
《梦雨斋读书记》(岳麓书社2005年3月版)里收入了黄裳先生的一部分古籍题跋。作者是国内有数的大藏书家,藏品以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以及清人诗文集为大宗。他的习惯是为所得之书写多少不等的题跋,除简要记录版本情况之外,多记得书过程,抒情议论的成分比较多,走的是清人黄丕烈(荛圃,1763~1825)的路子,而又颇有变化,成为一种新型的“黄跋”。在《关于题跋》一文中黄老介绍自己的做法和见解道: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逢买到一本新书(不论是新刊还是旧印),总要在书前书后写一点什么,至少也要在卷尾写下得书的年月。其中少成片段的就成了“书跋”。
……
藏书题跋是散文而不是学术论文,这是我的偏见。当然,专讲版本源流,版刻优劣的如陈仲鱼的《经籍题跋》之类,我也是佩服的,但总不是爱读物。如黄荛圃的藏书题跋,那才是理想的爱书人的恩物。这是随时可以浏览的散文……
陈鱣(仲鱼,1753~1817)的《经籍跋文》写得太严肃了,可读性不免比较差,黄荛圃的士礼居题跋则活泼灵动得多;黄裳先生本人更是自觉地把题跋当散文来写,当然其中也不乏学术内容,于是成为他大写文化散文(或者称为学者散文)的前期准备。
黄先生的书在史无前例中全部被抄没,于是他就根据存稿,手写到一种红格旧笺上;后来被抄走的书发还了一些,得以过录下来的题跋就更多,《梦雨斋读书记》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正因为黄先生的藏书不仅当初有一个各处奔走辛苦搜求的过程,后来还有一个全军覆没失而复得的特别经历,感慨自然更多,试看下列二例:其一,关于秋浦周氏珂罗版影印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先有1951年得书之初的一段跋语:“今冬宝礼堂藏书归公,自海道运归,入京之先,徐伯郊氏招余往观,匆匆得见宋本三十许种,皆精绝。此册亦在,已裱成册页矣。云烟过眼,未能忘情。乃今日无意中获此影本,抚印精绝,与原迹不累毫黍,观之忘倦。漫书卷尾。辛卯岁暮,黄裳。”到1983年,又有一跋云:“此为建德周氏所制。此笺犹是荛翁原椟拓出,余得之周今觉家散出群书中。后沦盗手十年,昨忽归来,展卷惊喜,恍如梦寐。叔弢先生近以所印《屈原赋注》见赐,此册恐自庄严堪中亦无之矣。是可珍重,不徒以故剑之情,依依不忍去也。癸亥冬至前日。”“沦盗手”云云即指被抄没事。
其二,1980年为《金陵卧游六十咏》作跋语云:“顾起元有《客座赘语》,记金陵故事甚悉。余有原刻,仅存四卷,《嬾真草堂随笔》诸集皆未见,藏家亦少著录之者。余去岁重游白下,撰游记十篇,忆有此书,以尚沦盗窟,无从取观,怅叹无已。近始获归,亟阅一过。起元为万历中人,所记较余淡心父子更早,可见金陵旧事,暇当补入一二事也。庚申芒种后一日书,距收得已三十年矣。黄裳。”“尚沦盗窟”亦指被抄没而未发还。“盗窟”一词是鲁迅曾经用过的,见于1924年《俟堂专文杂集》的题记,自为黄裳先生所熟知。
自己的藏书及其题跋,同黄先生撰写、修订有关文章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这里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说在游记文里古籍中的材料还只是某种生发点染之资的话,那么在专谈古书的文章里,先前的题跋就是极其重要的出发点或主干了。也举两个例子来看。其一,黄老1952年购得晚明怀宁阮大铖(集之,1587~1646)的诗三集八种,在第二年的一则跋语中写道:“十年来余数过金陵,深喜其地方风土,曾撰为杂记如干篇,于晚明史事尤喜言之。曾于暇日经行凤凰台畔,故家园囿,鲜有存者。乃忽于委巷中得阮怀宁故居,今名库司坊,当日之裤子裆也……大铖诸集刊于崇祯季年,板存金陵,未几国变,兵燹之余,流传遂罕。况其人列名党籍,久为清流所不齿。南明倾覆,更卖身投敌,死于岭峤,家有其集必拉杂摧烧之而后始快也。念当无由更得之矣。乃忽于书友郭石麒许见此,为南陵徐氏遗书,欣喜逾望。”稍后又有跋尾多条,从不同的侧面谈阮大铖其人其书,对于没有能够买到或借抄阮胡子的《和箫集》颇为耿耿。这些题跋内容非常丰富,可惜在《读书记》书中排列有些杂乱,最好统一按时间先后来安排。
阮怀宁集“文革”中自然在抄没之列,发还之后,黄裳先生1980年新写一跋云:
此《和箫集》今在天一阁。先是余曾商阁中主事者,请为议购,允以阁书十种赠之。后文化大革命起,其人乃密告余刻意求奸臣著作,并藏阁书甚富,遂遭抄没,群书尽失。此阮三集,近始还来,睹之兴慨,遂更跋焉。庚申五月廿八日,黄裳书。
原来黄裳先生藏书之被抄没,竟与他搜求阮大铖的诗集有绝大的关系。我以前曾经想,黄先生的书不在文革之初“破四旧”时被抄,却在数年后被一网打尽,颇不合于当时的一般情形;读此跋文可以得到一些解释,尽管其中仍多待发之覆。
这三集八种阮大铖的诗回归之后,黄先生很快写出了文章,这就是发表在《读书》1981年第6期上的《咏怀堂诗》,后收入《银鱼集》(三联书店1985年2月版),又编入《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和《黄裳文集·榆下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4月版),是黄先生的名篇之一,也是解放后第一篇谈阮大铖诗的重要文献。
在黄先生的藏书中,明末大文学家张岱(宗子,1597~1684)《琅嬛文集》诗歌部分的稿本(旧藏杭州八千卷楼)是价值最高的珍品之一,1951年初得时为之狂喜,写有题跋,略云“余旧好宗子文,然所获无佳本。今春偶得《史阙》稿本,又得康熙凤嬉堂刊本《西湖梦寻》,王见大刊巾箱本《梦忆》,今更得此,是所藏可谓富矣。”这是他极其得意之事。到1964年、1968年又分别写有长跋,对藏本作了考证和说明。1964年的跋后来以《关于张宗子》为题发表;而1951年跋、1968年跋再加上1981年新写的文章合为一篇,则以《张岱〈琅嬛文集〉跋》为题发表,二文均收进了《银鱼集》。1968年跋推测这部手稿流传的端绪道:
右凡五卷,自古乐府诗至五言律,通得诗三百又五章,宗子手稿本也……疑非全书,归八千卷楼时,即已如此。丁氏亦未甚重之……光绪中《琅嬛文集》曾有刻本,有文无诗,只古乐府曾刊入之,所据当是别一钞本。丁氏书光绪中由端午桥购归江南图书馆,由杭州载之江宁,入龙蟠里。名书重器俱无恙,惟词曲类及其他零星小册,颇有流失。当是端方幕府中人,择取精本,据为己有;或端午桥以之赠当国大老,皆不可知。此种书余得经眼或入藏者,凡六七种。
《张岱〈琅嬛文集〉跋》一文采用旧时题跋加新近文章合为一则的办法,这同《咏怀堂诗》根据旧跋新写文章的路径有所不同。采用旧跋加新文之法的还有关于《六朝文絜》、《蒹葭楼诗》、《太和正音谱》诸篇,均载《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一书,《翠墨集》(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中亦有若干。从这一类文章中最容易看出黄先生锲而不舍、与时俱进的特色。
作者多年买书、藏书、读书,反复加以研究,下过深刻的工夫,文坛旧事,烂熟于胸,最后才写那么一篇随笔。从《琅嬛文集》手稿入藏,到《张岱〈琅嬛文集〉跋》发表,前后凡三十年。真积力久,自然厚重深刻,且能“化堆垛为烟云”(钱锺书先生评语)。现在有人为了写所谓“文化散文”,临时搬弄,东拼西凑,难怪易出硬伤;或虽无明显的伤痕,而词气浮露,行文寒酸,堆垛功夫尚且不足,烟云灵动之势更是无从谈起,同样显得没有多少文化。黄裳散文之可贵,正由此种比较中得到说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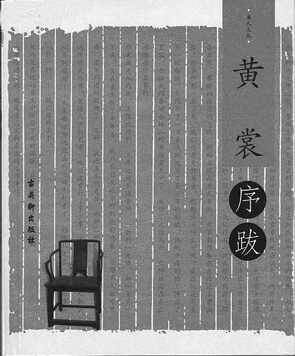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