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作家陆天明接续推出9部长篇小说,涉猎各种题材。他既探索过“纯文学”,也涉足过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话剧创作,还因《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反腐三部曲”和《省委书记》一书名声大震,与张平、周梅森并称为中国反腐写作的“三驾马车”。
10年前,年过七旬的陆天明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我有话要说。想告诉人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与民众一起改天换地为己任。他们也为此付出过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陆天明说,“而我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写“中国三部曲”。花费5年写《幸存者》,又花费6年写《沿途》,第三部正在路上,共同讲述一代人跨越40年的命运——他们到底是怎样活的,为什么要这样活,又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这完全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的。每一代都有这样一批人。屈原为什么要跳江?谭嗣同、秋瑾为什么要牺牲?李大钊为什么就义?陈乔年被施以酷刑就是不屈服。每一代都有……但以我们这个形式追求理想的是绝无仅有的一代……”如今已80岁的陆天明越说越激动。
陆天明经历两次上山下乡。1957年,14岁的他特意改户口虚长两岁,从上海到了安徽,为的是“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后来因病吐血,回到上海养病。其间,他积极上进,当了街道团委副书记。到了1964年,一批又一批上海青年响应号召,支援新疆建设。
此时的陆天明,拥有两种人生可能。第一种,按照街道党委书记说的,动员其他青年去新疆,他自己可以不必报名,留下来努力工作,成为正式在编的机关干部;另一种,和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边疆。他选择了后者。“我为什么要去?因为青春的冲动和激情,因为时代。”
因病回到上海那段时间,陆天明和一帮年轻人自发组织了一个“哲学研习会”,常常聚在公园里交流读书心得,还不定期研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中国该往何处去”“当代青年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家、国’二字在我们的生命中应如何安放更得当”,等等。
“写作时,那些过往、经历都冒了出来,经常是写着写着,眼圈就红了。”陆天明回忆说,他常常有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写作,是陆天明少时的理想。他从小爱读书,12岁时就有诗歌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过。他没读过大学,“我的‘中文系’是在图书馆上的”。当年,他从安徽回到上海养病,大概有一年时间,上午到街道团委工作,下午到图书馆看书。每天如此,雷打不动,“把图书馆所有俄罗斯文学中译本读了个遍”。
“关注中国人精神上的危机或困惑,呈现思想上的变化,是我写作的一大核心。当物质上富裕起来,灵魂该安放在何处?”陆天明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他去大学讲课或演讲,经常会讲一个事例: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有一面墙,上面都是殉难志士的照片,每个人都很年轻,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只要他们在自白书上签字,就会获得活下去的可能,但没有人签。“现在、今后,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陆天明反问道。
在文坛小有名气后,曾有人对陆天明说:“你们这代人已经走到尽头了,写作是没什么前途的。不可能再有什么大名堂了,往后就只能看你们的弟弟妹妹或下一代的了。”他不服,用3年时间探索实验文体写作,写出《泥日》。王蒙一口气读完,专门给他打电话,请他道歉,说“因为读小说不理睬夫人被批评了”;王安忆跑到他在上海的妹妹家,说“你哥哥写了一部好小说”;文学评论家陈思和评论他“用20多万字的篇幅写出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写的东西”。
王蒙说过,陆天明有一个充满悲剧感的性格,因为他有点像堂吉诃德,“忧国忧民,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年轻过,很年轻时就沉重地生活……但我们不会轻易地全盘否定自己。我依然有心中的理想,依然有需要坚守的东西。总有人要做些什么。”陆天明能做的就是写作,他曾经描摹过这样的自画像:一个独行者,背一把破伞在深山沟里踽踽踟躇。
(环球人物微信号 9.3 陈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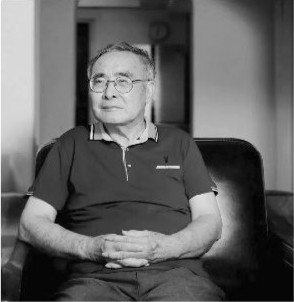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