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下笨功夫,就怕你不笨。这话是杨琥在清华读硕士研究生时,导师刘桂生教授常对他说的。从2000年接受编撰任务,到2020年年底《李大钊年谱》正式出版,杨琥用20年时间、135万字的成果向导师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今年7月29日,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名单公布,《李大钊年谱(上、下册)》荣获图书奖。
2000年,35岁的杨琥从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留校在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的研究室主任王学珍同时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会长。杨琥记得他当时找自己谈新工作时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是北大杰出的校长或学术先贤,校外的学者都在研究他们,可北大自己很少有人研究。“他问我,你愿不愿意编李大钊年谱?”杨琥欣然接受。在研读大量资料之后,他发现当时的研究现状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重复成果多,原创性研究少;概念性论述多,实证研究少;政治宣传性文章多,学术研究论著少。杨琥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要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李大钊。
在年谱的编撰过程中,不断对史料分析考辨,是杨琥面临的一大难点,尤其对于那些流传已久、深入人心的说法,他依然进行多方参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典型一例。
“这个说法出自上世纪80年代,是对高一涵回忆的概括。高一涵在上世纪60年代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讲述了1920年2月李大钊从北京护送陈独秀南下。后来学术界全部引用高一涵的回忆,其实这个回忆是有问题的。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出质疑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时高一涵人在日本,尽管他回国后胡适、李大钊都可以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但高一涵在文中明确说听到陈李二人在途中商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为了解决这个疑点,杨琥查阅了很多资料。“我又发现这个说法不是高一涵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而是1927年李大钊牺牲以后他在武汉追悼大会上说的,一个现场记者记录下了这一句。追悼会后,高一涵本人又写了一篇《李大钊同志略传》,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并没有提到相约建党这件事。而上世纪60年代那篇回忆里,他也没有提成立共产党。”
杨琥认为,“南下途中相约建党”的说法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是记者的记录报道,很有可能出错,从历史学角度讲又是一例孤证,不足以采信。“高一涵文章还说当时就李大钊陈独秀两个人离开,而且是偷偷地从朝阳门出发南下。但罗章龙的回忆又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时,还有十几个学生陪同他们出了德胜门。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只可以说明一点,陈独秀南下是一件秘密的事情,谁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只能存疑。”
杨琥分析,李大钊从1918年7月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2月出现建党的想法,可以说顺理成章。但对陈独秀来说,他的思想这时还没有完全转变,说他在离京途中与李大钊“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与他思想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
“陈独秀的思想真正产生转变是到了上海以后。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带来俄国革命的图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陈独秀阅读了这些著作,又与维经斯基深入交谈。之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叫《谈政治》,标志着他的思想真正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边。1920年8月他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10月李大钊建立了北京的党组织。如果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在南下路上确定的不能成立,那么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还是可以成立的。”
年谱的体例决定了以年记事,杨琥详细到月,甚至精确到每日,即便是日常活动也要记录进去。他认为,这些日常活动或许隐藏着重大的决策。他举了一个例子,1917年1月20日,钱玄同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李大钊的名字就是记录一次饭局:独秀今晚宴客于庆华春,同座者为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刘三诸公。
“这个时候李大钊还没有进入北大工作,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也不到一个月,但他在宴请沈尹默、刘三、高一涵这些旧友时邀请了李大钊,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密切。后来饭局上的陈独秀、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钱玄同这五个人都成为《新青年》的编委,经常在一起聚会。现在看来,这个饭局很重要!”
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朝夕相伴20年,杨琥为李大钊总结了五个突出特质:忠贞的爱国情怀、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头脑、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他的自然生命虽然已经结束了,但他的思想生命、文化生命、社会生命是长存的。”这也是他多年来追踪“谱主”轨迹的深刻体会。
(《北京青年报》9.1 颜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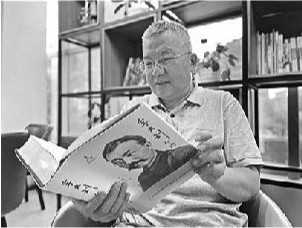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