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归根到底是要由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来书写的。在所有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中,学者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是人类文明自觉的创造者、记录者和传承者,是人类文明向新的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力量,且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良好的表达能力,其口述资料弥足珍贵。《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不仅展示了一位博通古今、融贯中西的历史学家的学术人生,记录了学者独特的为人为学为师之道,也以大历史中的个人视角,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个体生命中折射出的时代气息
刘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国难临头,亲历山河破碎之痛,立下“学术报国”之志。辗转求学,先后考取江南大学、南京大学、辅仁大学,毕业留校,传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
他经历抗日战争,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情景,许多无辜百姓抱着一捆稻草跳入长江逃命,却被淹死。上小学时,他经历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一些同学被打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和战争年代的一个缩影。
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形象?刘先生回忆,汪海秋先生就是比较典型的民国时期小知识分子形象。汪先生颇有才学,家境贫寒,两个儿子都读不起书,家里的蚊帐破烂不堪,他却能怡然自得,安贫乐道。
在江南大学时,唐君毅先生和妹妹唐至中先生都对刘先生十分器重,关怀备至,对刘先生的学术和人生有重要影响。1948年3月15日,学校组织学术讲演,在公益中学简陋的礼堂里,忽然听到一片倒塌声,现场顿时混乱。讲台上的先生们因离前门较近,很快就跑出去了,可是学生们一下就拥挤起来。这时,唐先生却不走,他穿着大褂在那里指挥,直到倒塌声停止,有工人过来帮忙,他才出来。刘先生说,唐先生讲的虽然是西方哲学,践行的却是王船山的儒家精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学术品格的形成
刘先生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与其良好的传统教育、深厚的国学根基密切相关。中学时期,时霖先生讲国文,就引起刘先生对词源学的兴趣。在江南大学时,刘先生听冯振先生讲文字学;钱穆先生讲中国史,提出要研究先秦诸子,必须有清代学术作基础。经过时霖、钱穆、冯振等诸位先生指导启发,为他今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转学到南大后,从刘永岳同学那里,他知道了南大的历史,知道史学界有“南柳北陈”,南方是柳诒徵先生,北方是陈垣、陈寅恪先生,他的视野更加开阔。
大学毕业后,刘先生在北师大当助教,李飞先生讲世界古代史,参考何炳松先生的《欧洲中古史》。刘先生一看,何先生的书参考了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欧洲通史》。鲁滨逊提倡新史学,梁启超先生也讲新史学,为什么叫新史学?这是针对德国兰克史学说的。他们认为,历史学不应该只研究政治、经济、外交等,还应该包括其他学科。
在刘先生看来,实际上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都是专门史。真正的新史学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讲的世界史,其实是西洋史,西欧中心论。这样的新史学,当然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然而,这却是中国史学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必须做出回应。
七十年学术研究、探索
历史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就是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过去西方人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写世界史,充满偏见,中国在世界史中没有地位。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写世界史,能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纯客观地书写历史?刘先生说,真正的人,都是现实的人,人们研究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现实服务。
当我们这代人刚开始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时,都严重地感觉到,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黑格尔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主张“西欧中心论”,中国人看了,也是不能认同的。黑格尔不是代表世界精神,他是代表日耳曼精神。在他的史学观里,中国注定就是要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一个征服对象。因此,刘先生也向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
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历史证明,证明自己存在、生存的理由是必要的,否则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是作了很多贡献的,对世界民族都有贡献。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历史是一个问题,从来需要多视角来看。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是这样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正认识一个世界,怎么能只有一个视角呢?中国的地位、中国的作用,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是有责任的,是有使命的,要为中国说话,要向世界作贡献的。我们要贡献自己的角度,贡献自己的经验教训。
刘先生说的这些,可以说是他逾七十年学术研究、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讲好自己的历史,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光明日报》8.12 全根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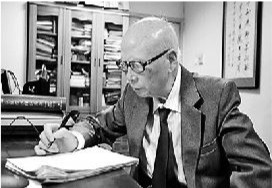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