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学者而言,《资本论》从一开始更多的是被当作经济学著作加以研究。在这种经济学研究模式下,人们默认《资本论》是一门具有实证意义、数学量化的科学,而非抽象的哲学。近十几年来,部分学者逐渐从哲学的角度解读《资本论》,这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担忧,认为“学界逐渐显现出一种将《资本论》阐释为哲学著作的理论倾向。这种倾向越过了‘《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巨著’的界限,导致了对《资本论》科学性的弱化”。对此,笔者认为,一是《资本论》所具有的科学性不会因为读者的解读有所弱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或掌握这种科学性;二是《资本论》的哲学解读不意味着不是科学解读,也就是说不能狭隘地将科学等同于经济学。
其一《资本论》所运用的方法有别于自然科学方法,并克服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局限,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研究在方法上的科学创新。《资本论》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通过把握“商品”这一抽象概念,展示了其内在所包含的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地租和工资等丰富具体的内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在结构和规律。通过这种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克服了自然科学中数学、实验、实证方法在研究人类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实现了精确研究与合理表达的统一,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其二,《资本论》所把握和研究的对象、内容不是意识形态的主观臆想,而是具有真实有效的客观现实性。与自然科学不同,《资本论》所要把握的不是由单纯物质性构成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
其三,《资本论》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现实的可预见性和历史的前瞻性。《资本论》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和矛盾的形成、发展机制,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
(《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1期 李逢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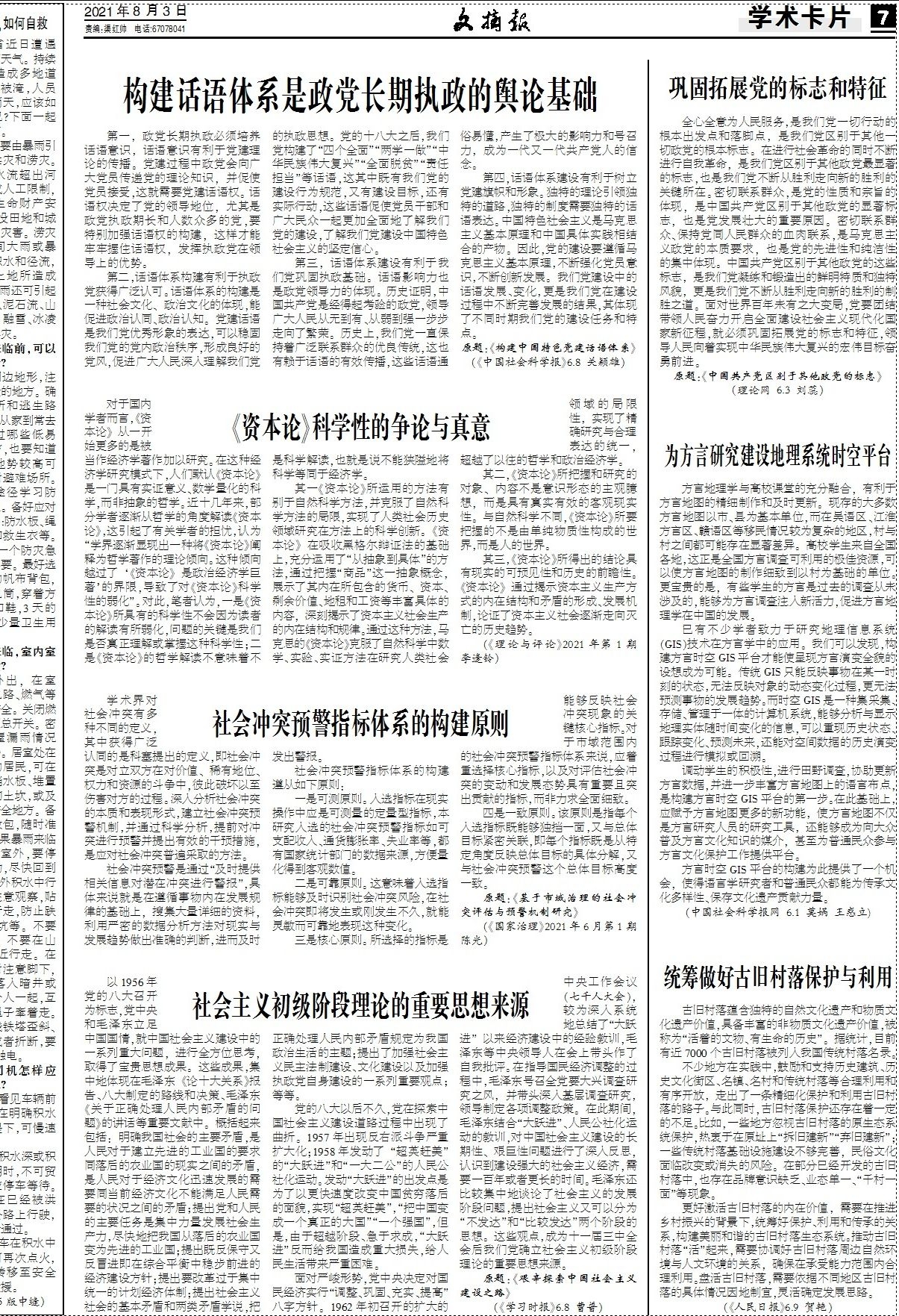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