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中国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与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即治国理政,地方治理是省市层级治理,基层治理则包括县乡村三级治理。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有自身的目标和要求,基层治理也有自己需要面对的特殊情境,那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省市)大一统的政策、体制、制度如何与复杂多样的基层治理生态实现有效对接,发挥中央(省市)与地方(基层)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省市)积极性,就是要使中央(省市)政策能够在基层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基层要有积极性,就是要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还能够激发基层治理的活力,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
县(区)一级要有政策转化空间。中央(省市)的政策、任务具有方向性、原则性和底线式的特点,要达到的是普遍、一般、共性的目标,而基层社会是多样性、特殊性、个性化的,如何将普遍与特殊、一般与特别、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就需要县一级有将中央(省市)政策、任务转化为本地政策的空间。同时,县域社会也会产生一些辖区普遍的治理问题和社会需求,需要县一级设置相关政策议题予以解决和回应。
乡镇(街道)一级要有机制创新空间。乡镇不是一级完整政权,部门设置不齐全,权力配备有缺陷。乡镇作为上级政策和任务的执行者,是国家体制与基层社会交互作用的真正“接点”,体制资源与治理问题在这里对接。
村(社区)一级要有村(居)民自治空间。在村(社区)内部,有许多事情、问题、需求既不能上升到县一级政策层面,也难以通过乡镇体制来解决,或者解决起来不经济。那么这些治理事务就得交给村(居)民自治来解决。
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是一个相对问题,实践中需要把握一个度,但不可能做到最适度,过宽的时候需要收窄,过窄的时候需要放宽。这也表明基层中国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理解基层治理时,既要将基层视为一个整体,又要对其进行解析,将县乡村贯通起来思考。
(《北京日报》1.25 杨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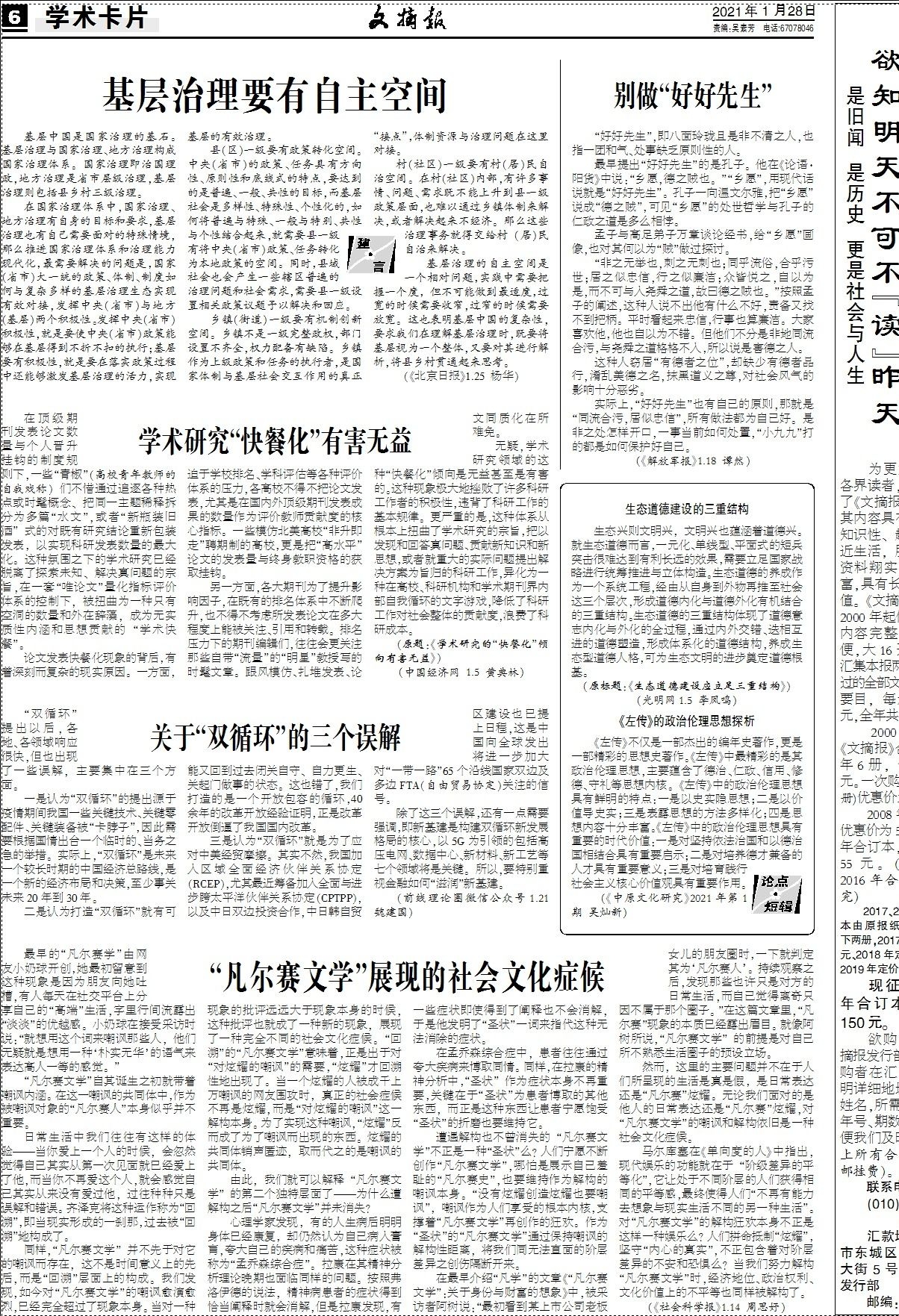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