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前的十月底,我由上海到了苏州,下车取了行李出站,人不多,站外停的只有极少的三轮车,其他都是黄包车,而且都很旧,有的还是死轮胎的,即车轮铁圈外,包一圈厚厚的有花纹的橡皮,不用充气。这种轮胎的黄包车,北京叫洋车,在北京早在民国初年就没有了,而苏州还很多。这可能因为苏州旧时都是石子路的关系……反正我就坐上这样一部黄包车,带上行李、拎包而去。一路上尖石子路,其颠簸是用不着说了,而最惊险的是下桥的时候,他大声喊叫着我听不懂的话,双足离地,两手像玩双杠一样,架在车把上,直向人堆中冲了下去,眼看着要撞到别人身上或小贩担子上了……但说时迟,那时快,他用手一摇车把,躲了过去,又向前奔了——这是我到苏州的第一个印象,迄今记忆犹新。
江南的冷,实在叫人难受。我从小在北方山乡,又在北京成长,漫长冬天,总是在有火的房间生活,古语说得好,“昏暮叩人水火,无弗与者”。我在到苏州之前,从未意识到冬天房中可以不生火,暖气是奢侈品。苏州第一次过冬天,又不停地下雨,又冻又湿,晚间又不习惯穿着大衣坐在房中,真是苦不堪言,一筹莫展,与几位同事便每天晚间去铁路饭店附近一家浴室去泡澡堂子,先脱光洗个澡,然后大家裹上大毛巾,躺在榻上,泡上一壶茶,天南地北地乱聊一顿,等浴室打烊时,再着衣回去睡觉。无锡人早上坐茶馆,晚上泡混堂,叫“早上皮包水,晚间水包皮”,我到苏州没有多久,便习惯“水包皮”了——冻得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不得不如此也。
我到苏州不懂苏州话,可不久就学会了听评弹,由听评弹不久又学会了听苏州话、说苏州话。在中南书场我认识了一位老艺人,叫周小春,当时已近六十,和一位年轻姑娘拼双档。有时我去的早,和他在台下聊天,他说战前听过刘宝全的大鼓,又说唱大鼓配大三弦,评弹配小三弦,问我听得懂吗?我说听得懂……娓娓而谈,如白发梨园,说天宝遗事,亦十分有趣。苏州当时,市民并不多,但类似平民化的娱乐场所特别多,书场、绍兴戏、扬剧、淮剧、锡剧、沪剧、电影院等,城内外四五十家,一般都客满,或七八成座。听书很便宜,雅乐、中南只一角,还管喝茶,小贩为你预先放一包香瓜子,只三分钱,连座位也占好了,你晚些去也没有关系。洋玩艺很少,当时北京盛行单位办舞会,上海舞厅尚有一二十家,舞客也不少。而苏州没有,只在北局有一家很小的音乐咖啡座,没有什么客人。
苏州当时民间穿戴,仍和解放前差不多,同事中有的老先生,冬天都是袖子管很窄的棉袍子,一般都是旧的,寒流一来,走在外面肩膀缩着,手也握紧拳头,藏在袖子管中,急急忙忙地走着,完全是叶圣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穿西装的也有,但都是旧衣裳,十分考究的很少了。女同事则都是夏天旗袍,冬天西装裤子、棉袄或绒线短大衣。女同学们用粗绒线织成大裤脚西装裤子,这在北京是没有看见过的。
(《云乡琐记》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 邓云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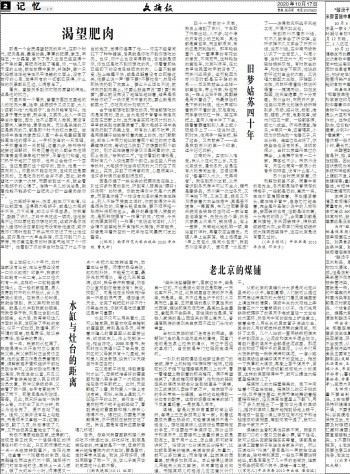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