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口音有着顽固的记忆功能,它往往与人的地域生存背景有直接渊源,口音越浓重,表明此渊源越紧密。从未有过远离故乡的经历,不觉得家乡的口音有什么好,很容易无动于衷。只有背井离乡,漂泊异地,人对自己熟悉的口音才变得格外敏感和渴念。
小时候,我在天津一所部队子弟小学寄宿读书,习惯于讲普通话,听到校外的人嚷着“干嘛”“嘛事”,觉得真是“土”到家了。我母亲的祖籍在四川巴中,很早就出来闹革命当红军,口音却一直未改。退休后,她成了街道居委会的大忙人,像是肩负了什么重要使命,其实也只是传达居委会的某个开会通知。她常常走家串户,不知疲倦地扯起悠长的嗓门,用浓浓的川音千呼万唤,直至一条长街上的所有家庭“无一漏网”。邻里的小字辈喜欢跟在她后面鹦鹉学舌,母亲却毫不在意,激情饱满,照喊不误。母亲的川音使我想到了这样几个词:泼辣、固执、勇敢、真诚,那样的好感逐渐扩展至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几位川籍元帅的形象,并延续至今。
我15岁那年当了一名小兵,军营在石家庄郊区,大家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练就了我一对善于辨别各地口音的耳朵。所有的方言中,最入耳的竟是过去我并不喜欢的天津话。我的天津口音带有“速成”味道,不那么标准,心里却感觉踏实。因为口音意味着一种认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本土地域的归属和接纳。一次,我去部队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战友,进来一个小护士,用天津话问候,我也用天津话激情回应。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老兵们总爱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复员回津后,置身于熟悉的口音却充耳不闻,“泪汪汪”的感觉更是荡然无存。
十六年前,我曾两次远赴美国探亲,加起来大约半年时间。那段日子,身居异国他乡,时常夜半惊醒,天津口音的“泪汪汪”感觉在我心里悄然复苏。记得邻宅住着一个女房客,湖北籍,单身白领,收入不薄,英语也佳,看似活得独来独往,沉稳笃定,内心的寂寞却似乎深不见底。某晚,她的房间突然飘来一曲《龙船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妹娃儿去拜年哪喂……哎,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间或,可听出隐约的呜咽声,很显然,那首湖北民歌的旋律和腔调勾起了她的乡愁。
一个机会,我还结识了旅居美国的台湾作家纪刚先生。据说,三毛生前有意继《滚滚红尘》之后,将纪刚那部在海外长销至今的著名长篇小说《滚滚辽河》搬上银幕,可惜没有如愿。年逾古稀的纪刚老先生操着一口浓浓的辽宁口音与我快意“唠嗑”。自谓少小离家,曾经沧海,早已心波无痕,说起1949年,国民党政府带着六十万军队撤到台湾,也带走了六十万个外省人的乡愁,那乡愁沉甸甸压在心口,有的时候真感觉喘不过气。然后,这位国民党老兵谈到自己的辽阳乡村老家,“乡愁病”骤然发作,以至于老泪纵横,那一幕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客居他乡的人越是身处天涯海角,口音的记忆越是容易频频造访,即使改了国籍换了身份,却改不掉换不了原先的腔调。它总会与遥远的乡愁丝丝缠绕,挂着泪,扯着心,独享在梦醒时分。
(《阅读是最好的独处》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出版 黄桂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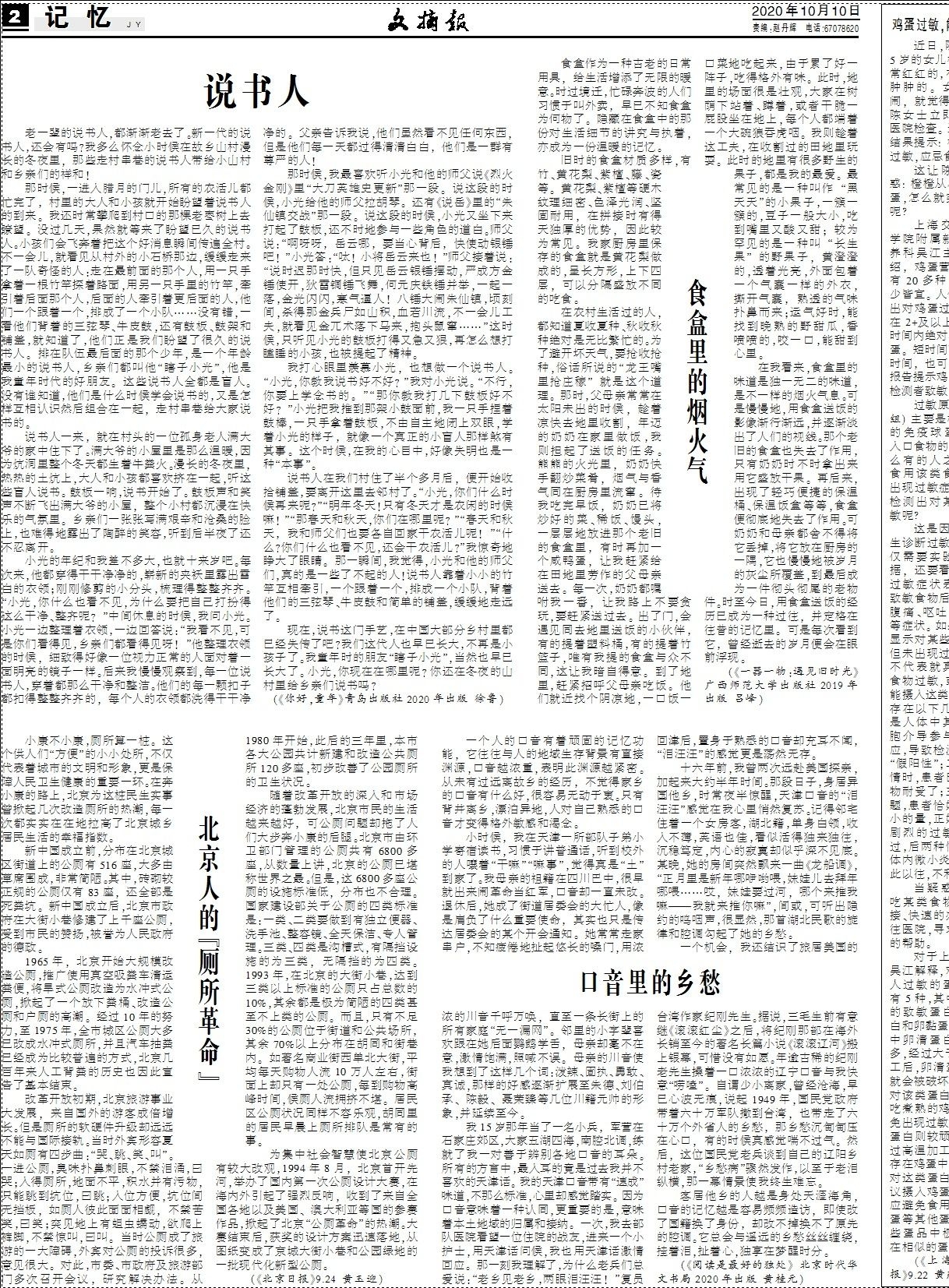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