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到少年期间,我曾多次去过我爸妈在贵州山间支内的地方。那是一座在山间的医院,从属于061基地。我只知道它距离遵义大约半小时的车程。以前从上海去那里的时候,是坐火车到遵义的一个叫“李家湾”的小车站,然后医院会派一辆解放牌卡车来接,到医院大约要半小时,但我从不知道医院的确切位置。
在上学前我大约去过贵州两次。一次大概是爸妈带我去的,我已不记得任何细节。我爸是1969年就从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即今上海市肺科医院)去的贵州,那时我还只有3岁。我妈在1971年,也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被调去贵州了。去的时候因为医院还是草创,生活条件很差,并没有带我去,我和两个姐姐一起留在上海,随祖父母生活。我爸说后来我妈看到上海寄去的照片,上面的我长得很瘦弱,眼睛下面都是黑眼圈,都快哭出来了,所以决定还是让我去贵州。那一次住了有多久,不记得了。
还有一次是我二姐带我去的,我却有一些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大约6岁,我二姐大我8岁,应该是14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我爸妈没有和我们同行,是托几个同事带了我们一块去的。
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通,火车从上海经浙江、江西、湖南,然后要去广西柳州绕个弯,再进入贵州。全程要三天四夜,是坐铺过去的。因为上海站是这趟上海到重庆的火车的首发站,而当时只有在首发站才能买到对号入座的票子,所以还能有个座位,算是好的。从半当中上来的,不管是多远的路程,在有人下车腾出座位之前都只能是站着、蹲着,或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刚上车的时候未免还挺兴奋。即便是坐火车,当时也是少有而昂贵的经验。我的多数小伙伴们都没有坐过火车,也没有出过上海,更不用说去两千公里以外的遥远的贵州了。尤其是听人说火车在经过钱塘江大桥时,可以看到蔡永祥的铜像——那可是我们都在小人书上读到过的英雄人物啊!他在火车飞驰而来的时刻,发现有一块大木头横在铁轨上,他奋力把它掀出了轨道,自己却倒在了车轮下。
那个时候车速慢,火车从上海开到杭州也要六个小时。当火车终于在我们的引领期盼下驶过钱塘江大桥时,我却并没有看到蔡永祥的塑像——也许是我坐在了看不到塑像的那一侧,也许是塑像其实并不在铁道边。
过了杭州,兴奋感慢慢减弱,车上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下去的人,总比上来的人少。上来的人,有的还是挑着担子的。有的是挑着行李,有的则是挑着当地的出产。我就看到过有人挑着大概有几十斤重的巨大西瓜上车。
等车厢的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和行李以后,列车员也就停止了扫地、拖地、倒开水等一切服务,卖食品的小推车也不再过来——事实上也无法过来。
我很快就学会了坐着睡觉。能趴在面对面的两排三人座位当中的那张小桌子上睡觉简直是个奢侈,但这张小桌子很短,只有坐在靠窗位置的人能够享受,上面还常常放满了各人的水杯和其他杂物。
半夜里在迷迷糊糊中醒来,吃惊地发现脚底下杵着两条裸露的脏污小腿。低下头一看,座位底下居然躺着一个人在呼呼大睡!
后来在车厢里走动时,看到像这样睡在座位底下的人还不少。而他们周围的地面上,则满是各种垃圾。当时的人颇喜欢在车上吃东西,即便是列车员刚扫过,很快瓜子壳、水果皮等又扔了一地。睡在地上的人,等于就是睡在垃圾里。
车更挤的时候,就连座位的靠背上,也会坐上一两个人。他们脏兮兮的脚,就垂在你的边上。
火车到李家湾站是在半夜,只停两分钟。而且因为是在基地附近,为了“保密”或“安全”起见,车站还不许亮灯。因此大家都很焦虑,怕错过了站,怕到了站来不及把行李搬下车。他们的焦虑情绪也传染给了我。
傍晚时,疲惫不堪的我躺在姐姐的膝盖上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大哭,而且是属于上海人叫“发魇”的那种,也就是小孩子毫无理由地在睡觉中大哭大闹。可怜的二姐,看着我束手无策。她那时也是个孩子啊,却要照顾我这个小小孩。
等我清醒过来以后,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慢慢平静下来了。后来到站后,人和行李也都下了车,没发生什么事故。现在想想,两分钟并没有那么短,只是在那种特殊情形下,大家都特别紧张罢了。
(《文汇报》3.11 谈瀛洲)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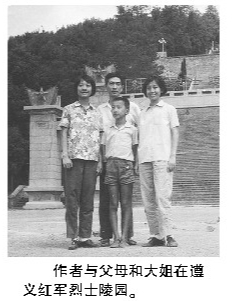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