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藏书界,韦力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7万余册,四部齐备,其中不乏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等珍稀善本。甚至一些过去被学者认为早已不再存世的古籍,也完好地收藏在他的“芷兰斋”里。他的好友、中国古籍拍卖事业的开拓者拓晓堂先生说:“韦力是一位不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藏书家。”
一个人的寻访之旅
30余年的积累,让韦力的收藏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高人一筹。他所珍藏的7万余册古籍,按照中国古籍经、史、子、集的内容分类,不乏珍稀孤罕之善本。藏书之外,他还以不同寻常的文化寻踪探源之旅和异常勤奋的写作来“反哺社会”。如今,他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已出版到第六部,共计400多万字。
谈到“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的缘起,韦力说,1997年前后,某杂志刊发的一篇关于藏书楼的文章中图文存在错误,激发了他亲自认识藏书楼的冲动。
韦力耗时4年遍访典籍中记载的163座古代个人藏书楼,又花3年时间逐一查证。在三卷本115万字的《书楼觅踪》中,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沈括的梦溪园、顾炎武的读书楼、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曾国藩的富厚堂、顾颉刚的宝树园、叶恭绰的幻住园皆被揭下时光的面纱。
寻访藏书楼之外,他还完成了对几十位古代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的寻访,在《书魂寻踪》序言中,他写道:“能在他们的墓前鞠躬致敬或献上一束鲜花,已经感到满足。有时我会坐在这些墓旁守候一刻,静听山风吹过松林。每当此时,我心中都会想起那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
“一个人的寻访之旅”充满艰险。2013年4月24日,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寻访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当他在寺院内察看石碑时,突然,身边的一块功德碑倒下来,砸中了他的左脚。身处荒野,无人相助,他抓起身边的一块塑料布,拧成绳勒住了腿。治疗更是凶险,截肢后伤口不断感染,难以愈合,5次大手术后,韦力左腿膝盖以下被全部截掉了。
这次意外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认为能做的事还是要尽量做完,人生无常。此前没有完成的书稿,开始一本一本地写完。
“藏书不可不贪”
韦力至今珍藏着自己拥有的第一部古书。那是1981年,他念高一,古籍书店刚恢复。他在那里看到一套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是康熙五十四年故宫刻印的,漂亮极了,卖80元,是书店里最贵的书。他把家里给的吃饭钱一点点攒下来,凑了几个月,终于买下这部书。这也让他明白,买书必须有钱。
“很多人认为我是因为有钱才藏书,其实恰恰相反,藏书没钱,才想办法怎么让自己变得有点钱。”韦力曾在天津工作8年,那时天津正大力发展开发区,他26岁就当上中国外贸总公司下属三资企业的总经理,后来又自己办公司,有了点积蓄后就全都投到古籍收藏这个爱好中。
在韦力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是买书的黄金时段。改革开放后私藏复苏,最直接的得书方式,是古籍书店。那时他去古籍书店的频率极高,若几天没进书店,就有怅然若失之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古籍书店大多会在各种节日放出库存,韦力将其喻为“爱书人的狂欢”,他会到各地收一批书回来。
得书的另一渠道主要是向私人购买,尤其是大藏书家的后人。有些大家之后卖书,听说韦力不是做古书生意,而是真心爱书,都愿意将几代人的珍藏之书卖给他。
后来有了古籍拍卖,拍卖市场重新构建了古书价格体系。韦力的不少书是在拍卖市场上经群雄逐鹿后而得,在《古书之爱》中他写道:“有些书多年来朝思暮想寤寐思服,蓦然回首,拍场预展中,与书相对,那种怦然心动之感,绝难用语言形容得出。此时占有欲高度膨胀,必欲得之而后快。”
“我只是这些书生命中的一小段”
与古代藏书家不同的是,韦力从没在自己的藏书上加盖过私章。“我只是这些书生命中的一小段,所以尽量保护好、传承好就可以了。”
“芷兰斋”的古籍未来的归宿是哪里?韦力的回答是,来自于社会,然后重新归回于社会,重新散在天下。很多人会认为捐给公共图书馆,当是最好的归宿。韦力不这么想,“现在公共图书馆的古书数量占了总量的95%以上,公藏的古籍再也不会在市场上流通,也无法再让人亲近和把玩。我在藏书过程中,最快乐的就是获得书的过程,我希望今后的藏家能继续享受这个过程”。
(《文汇报》2.16 李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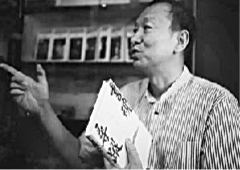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