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中清是历史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近日,李中清教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父亲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辈子逃不出父亲手心
记者:你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有没有要求你也一定要成为大物理学家?
李中清:小时候,父亲也曾花时间辅导我学数学。每当父亲坐在我身边时,我就紧张得脑子一片空白。父亲考过我,给我出了一些数学题,但觉得我不适合。后来父亲也不指望我成为一名数学家。我弟弟比我聪明,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和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子女相比,我感觉压力比他们小得多,父亲没有拿他的成就来要求我们;甚至和普通家庭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小,我和弟弟想上任何专业都可以。但和所有父母都一样的是,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只要考试没考好,回家他也会很生气。
高中住校之前,我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我当时想,一定要选一个跟父亲不同的专业领域,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太出名了,我要跳出去。
选择历史也是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美术、历史等一直很感兴趣,家里收藏着几百件古董。在我15岁住校之前,每个月全家要上博物馆,看艺术展。他觉得美术和真理一个抓牢直觉,一个抓牢理性,异曲同工。
我跟父亲说,我选了法国历史。他就找了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发现没有中国人。然后说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研究他们的历史,应该做其他国家的历史,建议我考虑中国史。所以,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我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过。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我想逃开父亲的影响,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心。
现在,我儿子学的是医学,女儿学的是艺术,大家的领域各不相同。
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记者:顶着诺贝尔奖得主之子的光环,会不会压力很大?
李中清:父亲得诺奖的时候我才5岁。得了诺奖,对我们家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因为父亲太低调了,不喜欢显摆,我直到10岁后才见到那个奖杯。
父亲年少成名的压力会存在,但并没那么直接。好在我和弟弟都还混出了一些名堂,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我和我儿子有时候讲,不想做院长,想做研究,看能不能进美国科学院。儿子跟我说,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做一些事情,能改变世界。
记者:你父亲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李中清:父亲今年91岁了,5年前才退休,从纽约搬到旧金山。父亲退休后我以为他会回中国,跟大学生在一起,但是他却真的退休了。刚退的时候还做物理,后来他告诉我,错误率太高,不能做计算。于是他做以前教研究生时的习题,没事就在家里算这些东西,后来也算不清了。他就看以前写的文章、公式,想通过动脑子确定他的生存。他最后发表论文是快87岁时,发在国外的物理学期刊上。
他身体总的来说很不错,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这些。但毕竟90多岁了,以前积累的小病都回来了,抵抗力下降。他每个星期会有两三次去公园散步,走1~2公里。每两周会跟我的女儿在外面画画。
父亲不给我们留一分钱财
记者: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对你有哪些影响?
李中清:他从来不是为了钱才做学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才能出成就。我们家很多值钱的东西都给中国了。他在上海的房子3年前已经还给中国了。那个房子原来是外公的,现在值三四亿元,保持了原有的结构。房子的位置非常好,有花园,有两个车库。光住的地方就有300多平方米。但把这么值钱的房子捐出去,他丝毫没犹豫过,也从来没考虑过给子女留财产的问题。我们也支持他的决定。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也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北大给父亲分了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那里很少有人住,只有我儿子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会去住一下。我从来不去住。我如果住的话,父亲会不开心。因为他从来不占一分钱的便宜。我当长江学者的时候,给一位领导讲课,讲了20多个小时。我让父亲给我一些建议。他说,做学问要真心做,一定要纯粹。跟钱扯上关系,就会把世界观带坏、带偏。
我和弟弟说,父亲的任何财产我们都不要,有的话也给第三代,跳一代。对于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太多了反而不好。我们得到的物质上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但精神世界会很丰富。
(《广州日报》11.2 肖欢欢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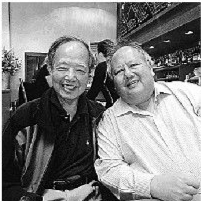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