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拉萨,我们这批援藏干部集中下榻在拉萨市工人疗养院休整。当晚我急忙到附近找长途电话亭,好不容易与女儿通上电话,因当时剧烈头痛,至今都回忆不起我说了什么,只知我醒来时,躺倒在电话亭的路边。生物学家早已断言,人到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将难以生存,并把这一高度,确认为“生命的禁区”。
我对口支援的西藏那曲地区,地处藏北,平均海拔为4560米以上,自然要划入生命禁区行列。那里空气里含氧量仅为内地50%,一年需九个月要靠烤火度日。
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对我们援藏干部十分关心,送来的见面礼,既不是吃的东西,也不是穿的用的东西,而是一本厚厚的高原保健书籍。这份礼物,对初到高原的进藏干部说来,送得正当其时,是无价之宝。
那天,那曲镇藏民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我们。我被援藏单位人员抬下车,他们问我行李在哪里,我糊里糊涂说:“不要了,只要人在就好了!”
我在藏北住在一间铁皮房子,一边靠墙放着床,一边靠墙堆着牛粪,房子中间是烧饭取暖的牛粪炉。藏北的唯一燃料,是牛粪。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常常可以捡到牛粪。牧区老百姓,习惯用手把湿淋淋的牛粪,贴到墙壁上,晒干后替代柴火。藏北的机关干部,每年每人计划供应牛粪仅两车,超出部分自己去市场买,大约300元左右一车。
那曲,其藏语意为“黑河”,这里的水是白色的,氟和汞的含量特别高。在那曲烧开的水,通常不会灼伤人,因为水烧到摄氏七十来度就开了。烧开的水,通常混沌如泥,可能是矿物质偏高。这里的井水,即便在夏季,也冰冷刺骨。如遇洗衣服洗碗等,一定要把水加热,或戴上皮手套。冬季要吃点井水,尤其不方便,那井口永远都是数尺厚的冰层覆盖着,需用铁锤、斧头将冰层砸开。
吃饭,在高原一直是令人头痛的一件事。这里的单位一般不设公用食堂,烧饭炒菜,如果离开了高压锅,只好吃生的。
要在那曲吃上新鲜疏菜,的确比登天还难。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张凤蛟在那曲军分区任职时,曾许以重奖:谁能在那曲栽活一棵树,记三等功一次。我一到那曲,也曾投入到植树造林活动,几度春秋,各种努力都尝试了,树苗竟无一成活。
1996年,我在藏北高原援藏工作之余,写了一本25万字《走进西藏》的文学作品、一本30万字《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书稿,后均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刻在高原内外引起轰动。在这里,人们轰动的不是关于我书的内容,而是关于我在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是如何写书的?
到那曲没几天,我不等身体恢复,就到岗上班。办公室设在二楼上,第一天上班,从一楼到二搂,我足足爬了半个多小时。也就是从这天上班起,我正式开始了业余写书的行动。
先是寻找稿纸,我工作的单位里没有稿纸,后来才发现,整个那曲镇的大大小小数十家小店,从未卖过方格稿纸。我这才后悔,到高原写作,带空白稿纸比带资料更要紧。我向女儿求救,要她将在杭州买的一大叠作文薄,先借我使用,并答应在上面写她最喜欢的故事。
用墨水写字时,我的第一瓶墨水仅用了七天。向人打听,是因那曲气候干燥,墨水瓶打开后,不及时拧紧盖子,墨水中的水分很快就挥发掉。而到冬天写作时,又很滑稽,墨水与瓶子永远冻在一起。自来水钢笔在这里,一管墨水打满,写不了几个字,笔尖上的墨就结上一层硬壳,有时为了提高写字速度,我干脆把钢笔作蘸笔用。
在高原写作,我总感到脑袋特别笨拙,特别迟钝,很难产生灵感,记忆力很差,许多常用字也会写不出来。到北极采访过的新闻工作者王迈,1996年9月来到高原采访,他特别提醒我:“千万别在高原过度用脑!”
关于在生命禁区里到底能否写书的争论由此而起。好在我写作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些。我一直以为,“三年援藏是有期的,但把一个真正的、博大精深的西藏反映给世人,可能是最大的援藏,而这又是永远无期的。”为此,西藏归来,我几乎牺牲了全部业余时间,精心研究西藏,全力书写西藏。
当我的书正式出版时,我在第一时间,将我在生命禁区写作的第一本书郑重送给了我的女儿。因为我答应,要用她的作文本纸,书写出最美的故事!
(《致青藏》江苏文艺出版社 张国云)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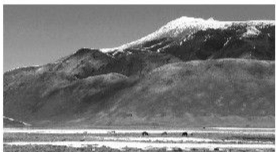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