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考进北大东语系,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系主任季羡林教授。瘦高身材,穿着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而我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说明我们的机会难得,担子很重。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总之,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派头”。
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听课真是一种享受,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
1969年秋天,他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
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季先生在北大从教60余载,几代学子受到恩泽。几年前,师弟王邦维有一篇纪念文章《师恩如父》,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
1981年,我作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那时先生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一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2001年11月19日,天气阴冷,刮着三四级北风。师兄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永乐大钟上铭刻的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先生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那时候他已经患病,只是不动声色,在那里硬撑着,12月9日就被送进301医院。
事后我对季先生说:“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先生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季先生对待学问和学生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在他的指导下,张保胜教授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将大钟上的梵字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
季先生晚年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孤独凄清,失去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身不由己。他本人却保持难得的清醒。
1999年在北大勺园为季先生庆祝米寿的宴会上,来宾致祝词以后,寿星致答词:“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当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著文坚辞三顶桂冠;他还郑重申明:“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先生一生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将之奉为良知并身体力行。他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世人楷模。可是先生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英雄业绩。“麟凤”也好,平凡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非凡与平凡于一身的人。
(《光明日报》2.6梁志刚)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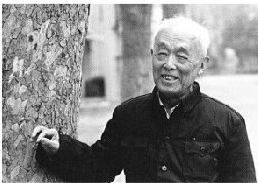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