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的阅读,出现了去经典倾向。大众文化的流行挤压了读者自由的空间,读者无条件地投降了,交出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自由裁断权,听凭大众文化的指挥摆布。阅读越来越没有自主性,再加上碎片化、快餐化、浅易化、感官化的阅读,久而久之,读者的判断力、理解力下降,想象力贫乏,逐渐失去了接受经典的能力。在这样一种阅读趋势下,经典必然受到冷落。
经典究竟值不值得读?有没有魅力?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我认为经典的魅力至少在三个方面。
经典魅力之一:探索精神
经典具有一种探索的精神。无论是对已知世界的解释,还是对未知事物的求索,经典都充满了强烈的探索气息。
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写的是个人成长中的善与恶,这本书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就在于它对人性以及人性与社会制度关系的探索。此书真实地描写了卢梭的下流行径。他说谎,行骗,调戏妇女。还有叫他一生都感到不安的嫁祸于人。16岁时,卢梭曾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当仆人,他偷了一条丝带,却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仆人的不幸。他抛弃朋友,他偷东西,以致形成了偷窃的习惯。他为了混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此书的经典意义何在?就在于它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卢梭通过个人的真实历史,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此书的经典意义更在于它对人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探索。它试图说明:人性是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改变的,好的社会制度会使人性由恶变善,坏的社会制度会使人性由善变恶。作家由一个天性善良的阳光青年变成了一个充满了龌龊的青年,实际上是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与《忏悔录》异曲同工,带有明显的人性探索色彩。《沉沦》的主人公热爱自然,热爱文学,多愁善感,颇有才华,性格忧郁而又柔弱。由于追求自由,反抗专制,而被学校开除,不得不留学日本。主人公的遭遇,使他患上了抑郁症,陷于自闭之中。于是他在十分孤独、十分痛苦的状况下,陷入性幻想,自慰,窥视女人,窥视做爱,甚至走进青楼,以致痛苦不能自拔,投海自尽。小说一发表,就在文坛引起一片哗然,许多人批评这篇作品是色情小说。其实,这部小说在我看来是在写人性,写人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揭示了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到了日本,融入不了那个群体,不能接受那个民族的文化,加之处于青春期,于是陷入了孤独苦闷之中。此篇小说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经典魅力之二:耐读性
经典为什么耐读?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面特别强调“陌生性”,书有陌生感,才会引起读者好奇,具有吸引力。从陌生性的角度分析,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无须重写的书。《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写有《王蒙活说红楼梦》,他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阅读《红楼梦》。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不同人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会因为个人的修养、文化背景不同,所得也有所不同。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经典就是人类思想的策源地,就是人类文明的发生地,经典必须是深刻思想的所在。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和《论语》《孟子》,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把柏拉图和莎士比亚作为传统正典里面的正典,而把卡夫卡作为西方现代正典里面的正典。为什么给卡夫卡这么高的地位,把他放在经典里面的核心位置?就在于卡夫卡小说隐含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深刻的思考,如《城堡》。故事很简单,K是主人翁,K多年前被伯爵聘为土地测量员,千里迢迢到城堡报到,但是到了城门却不得其入。守门人不知有土地测量员这个人,也不知有伯爵聘用这回事,于是K就留在了城堡外面的村子里,天天想要进入城堡。高更年翻译这部小说,“前言”里介绍了《城堡》主题的十四种说法。如果从隐喻式的角度解读,“城堡”确实具有象征性。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说,卡夫卡的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人的存在和意识之间的罅隙,用卡夫卡的话来说:“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人生尴尬是卡夫卡的小说表现的重点,而这种人生的尴尬和困境,就来自意识与存在之间的矛盾。人不可能有任何预设的目的,因为人的任何目的都是非真实的,然而人却永远希望这种目的的存在,于是就产生了“预期——他们的和我们的——为实际上的、现实的世界所阻挠”,K永远也进入不了这个城堡,意指人永远也达不到他的目标。
还有,读卡夫卡的小说,我们会感到:每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都是偶然的,都是一个唐突的外来者。他想融入这个世界,然而在这个世界之上,个体永远是个外来者、局外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疏远,如此之互不相关,如同K与他周边人的关系。我们看他的小说,就可以看出人的存在荒诞性,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陌生。K在村庄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弗丽达,弗丽达是城堡的官员克拉姆的老情人。K之所以和她交往,就是想通过她接近克拉姆,解决他进入城堡的问题。同样弗丽达失宠,想要交往个外地来的陌生人,以引起克拉姆的重新注意,也是在利用K。这对男女的朋友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网络社会,这是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按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应该是越来越缩小、亲和感会越来越强。而实际情况是人更孤独了,人与人间的关系更冷漠了。从《城堡》对人的关系的描写,已经预见到了人今天的生存状况。
经典魅力之三:超越性
经典的第三个魅力,在于其超越性。经典作家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不管现实多么好,但是在经典作家眼里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经典作家在其作品中常常要解剖和批判现实,批判性和超越性就成为经典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对经典的阅读,无非是两种解读形式。一种是前面所讲的隐喻式的解读,一种则是历史式的解读,作者写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结合历史环境来解释。如果作历史的解读的话,《城堡》写权力的无所不在,批判官场的腐败,的确十分深刻。自小说的第十五章开始,卡夫卡集中描写了官僚机构内部的运作机制,档案的投放、积压和处理的随意,文件办理的拖拉和无序:“可是城堡在这一方面办事拖拖拉拉,而且最糟的是你永远不知道拖拉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这件事正在办理之中,但也可能根本还没有着手办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K的身份不明?就是官场的运作。就在伯爵向K发出聘令的同时,村长却不同意聘土地测量员,是否发出了村长反对的文件?不知道。发出以后到没到K手上,也不知道,这样才造成了K的身份不明。再看看卡夫卡如何写权力的无所不在。四月份有个救火节,城堡里面的官员都出来了,其中就包括救火的官员索尔提尼,他看上了村里的漂亮姑娘阿玛莉亚,却遭到了姑娘的拒绝。从此,阿玛莉亚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这个家庭原本是做生意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企业家了。但从救火节后再也没人到他们家做买卖了,交易没了。父亲四处告状,但你去告谁呢?没有一个官员、没有任何文书命令村民不与阿玛莉亚家来往,总不能让城堡里的官员发下文书命令大家与阿玛莉亚家做买卖吧。写官场权力的无所不在,像无影无形的网,吃人不吐骨头,写得极深刻。
经典不只是批判,它也要给人们指明方向,提出解决方案。如托尔斯泰,学外国文学时,老师很少肯定托尔斯泰主义,多批判之。托尔斯泰提倡“不以暴力抗恶,用爱融化一切”,似乎是一厢情愿,似乎很幼稚。但面对当今的现实,我越来越认识到了托尔斯泰的伟大。佛克马说,安全和自由是需要经典关注和解决的,其实经典早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再看托马斯·哈代,他的作品里充满了一种博爱精神,一种对弱小的怜悯之心、慈悲情怀。他写了《无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丝》等小说,他说过一句名言:“你这可怜的灵魂啊,我的胸膛就是你的卧榻”。我看过之后极受感动,这种胸怀我们在现在的作家作品里已经很少看到了。还有狄更斯,号称灵魂大师。他确实就是想为我们的灵魂寻找出路。
经典作家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不满,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完美,他的批判的意图是来自于他向善向美的心理。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经典的作家,用他们的作品来感染我们这些读者,浸润我们这些读者,才使我们这个社会既充满了丑恶和暴力,同时也使这个社会向善向美,使我们的社会永远有一个前行光明的道路。这是经典魅力的根本所在。
(《光明日报》10.27 詹福瑞)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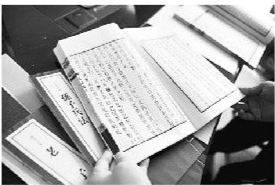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