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末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病房,李储文先生正在读书。生于1918年的李储文,已近百岁,虽然行动略显迟缓,但饮食如常,记忆力尤其不错。
初见周恩来
记者:1937年,你考上了上海的沪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怎么样?
李储文:沪江大学当时的商科与化学系教学水平名列上海之首。
我的大哥要我念化学,毕业后到煤气公司工作,他觉得这样比较有前途,能够实业救国。
记者:当时局势怎么样,社会上的抗日情绪已经起来了吗?
李储文:当时,长城抗战早就开始了,淞沪会战已经失败了。其实在1935年底,为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发出了“抗日救亡”“一致对外”的号召,上海复旦、交大、光华等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时我还在光华大学附中上学,就参加了抗日游行。
记者:1941年,你离开了上海?
李储文: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已经撤到西南大后方,主要工作是为抗战军人服务,开展学生救济工作,那里很需要人。我和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执行干事江文汉假装是亲戚,一起逃离了上海。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在中国基督教界很有影响。我们先逃到芜湖,然后就一路向西。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就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还负责《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他的身份是公开的。后来,我在重庆七星岗的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周副主席,当时很激动。
记者:周恩来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是一个普通的进步青年,忽然见到中共的副主席,很拘谨。恩来同志非常懂得我的心理,他拿了一些重庆特产的小柑橘和小花生,说:“坐,不要紧张哦!我问,你们说。”这样我就不太紧张了,完全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恩来同志让我去缅甸,到中国远征军中服务。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远征军中设有军人服务部,恩来同志让我以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到远征军中去做工作。他把到缅甸之后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写在一张糖果纸上,和一堆糖果混在一起,他说你要记住哪一颗糖果。
记者:然后你就直奔缅甸了?
李储文:先去昆明。那时的路特别难走,从重庆到昆明还是趴在卡车顶上,经过遵义、毕节,停停走走花了一个多月。
到了昆明才知道,昆明经腾冲去缅甸的路已经被日军破坏,没法去了。当时江文汉已经在重庆的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他建议我去云南青年会。我向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龚澎报告了,她让我留在昆明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进入西南联大
记者:你后来怎么进入西南联大的?
李储文:正好云南青年会有位干事认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他带我去见梅校长。
我自我介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想在这里办一个学生服务处,专门为老师和学生服务。他说我明白了,可以试着办。然后他划给我一块荒地,就在学校边上,其他什么也没有,都要靠自己想办法。
记者:你的学生服务处主要提供哪些服务?
李储文: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和理发室等,虽然设施简陋,但还能适应同学们的需要。阅览室订了五六份报纸,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记者:据你观察,当时学生最爱看什么报纸?
李储文:那还是《新华日报》,因为它真实,比较客观地报道抗战进展,也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不少学生家乡沦陷,跋涉千里,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昆明,他们远离父母,甚至与父母失去了联系。当时物价飞涨,学生们经济拮据,学习与生活异常艰难困顿,有些学生衣食无着。但大家心气都很高,坚决要求抗日,不少人很同情共产党。
记者:除了提供报刊,你还为他们做什么事?
李储文:那时候我夫人章润瑗从上海过来了。她来了我就有了帮手,我在想,能不能为学生们提供一顿早饭?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同学每天上午都空腹去上课。
我们做的早饭很简单,每个学生是两个馒头和一碗豆浆,由我夫人负责,每天请两个学生帮忙,还请了三个工人清早三四点钟就开始做馒头。收费非常便宜,低于成本价,因为有教会的资助。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人来吃早饭。有一次做馒头发面发不起来,把我们急死了,那么多同学等着吃啊!
记者:除了提供生活和医疗服务,你当时还怎么做学生工作?
李储文:我经常跟同学们聊天,就是倡导他们做正派人。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凡是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为人都很正派。学生服务处尽力支持同学们的民主运动,像学生话剧演出,我们提供旧沙发给他们做道具;同学们要举行游行抗议,就在学生服务处写标语做传单。
为了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大家互相合作,情同手足。
骑“洋马”送钱
记者:你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交往多吗?
李储文:当时昆明有个金铺老板姓熊,是个爱国商人,他想为教育做点贡献,每个月为西南联大的几位知名教授送点钱。
这个熊老板很相信青年会,他把这事托我们做,因为他不想留名。在青年会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很相信你。这个送钱的事就由我来做,我每个月骑着“洋马”,前面有一个篮筐,放一些吃的东西,下面都是钞票,挨家挨户地给几位教授去送。
记者:主要送给哪几位?
李储文:有不少人,像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叶企荪等等。
记者:你跟谁交往最多?
李储文:闻一多。他原来住在校园里,房子很小。华罗庚家遭到日本空袭被毁后,一家人住进了闻一多的家,两家人十多口,合住三间房。
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在追悼会上讲,你们谁是特务,有种的站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在那时候,这种话没有人敢讲的,所以我说他是诗人气质,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记者:国民党特务是不是很早就盯上闻一多了?
李储文:在闻一多遇刺之前,国民党特务就在昆明一个叫“日昇楼”的城门上,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的是“闻一多夫”。因为苏联人的名字大多有个“夫”,特务们说闻一多拿了苏联津贴,是苏联间谍。其实这怎么可能,他是条硬汉子。
记者:你具体怎么做这些教授的工作?
李储文:我利用每次送钱的机会跟他们聊,告诉他们不要只看国民党军队,我们还有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也很有战斗力,在跟日本鬼子顽强战斗。我促使他们参加符合他们身份的抗日活动,还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群众,目的就是要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引见毛泽东
记者:当时你是怎么开始跟美国兵交往的?
李储文:我在昆明住下来以后,恩来同志交给我两大任务,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努力。
因为青年会的关系,我认识了昆明当地一位主教,他家里经常办派对,有不少美国兵来参加,在这个场合就认识他们了。跟我熟的几个都是“飞虎队”的地勤人员,主要是测绘地图的。他们表示想访问延安,想见见毛主席。
记者: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三位美国兵,这件事当时国际影响不小,具体经过怎么样?
李储文:抗战胜利了,这三个美国大兵准备回美国,他们先到了重庆。正好我也去重庆出差,听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来参加重庆谈判了。
我想,这是帮助美国朋友实现愿望的好机会。我向龚澎同志做了汇报,请她向周副主席、毛主席转达他们的愿望。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欣然同意会见这些美国大兵。
1945年9月16日在红岩村,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后来龚澎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很高兴。三个美国大兵送的香烟被工作人员分了,毛主席看了哈哈大笑:“美国大兵送我香烟比赫尔利多,可见美国统治阶级代表和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友谊是不一样的哦。”
追忆与感慨
记者:抗战胜利的那天你在哪里?
李储文:我就在西南联大。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大家都高兴极了,学生们都在欢呼,我也是无比激动。
记者:现在每天喜欢做什么事?
李储文:我的最后一个公职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1988年退休。现在我老了,每天看《东京审判》。这套书就是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记录,是英文影印版,我花3万多元买了一套,总共80本。这套书很真实,详尽记录了当年的庭审经过。
记者:70多年后,现在回忆那段抗战岁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李储文:我记得就在抗战胜利后,恩来同志问了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时美国已经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了。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美国扔了原子弹。
恩来同志问我,你对这怎么看?我说,我还没想明白。恩来同志讲,那个说法是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被打败,就是因为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抵抗帝国主义,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铭记我们为和平所做出的奋斗和牺牲,珍惜今天的生活,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
(《解放日报》10.11 高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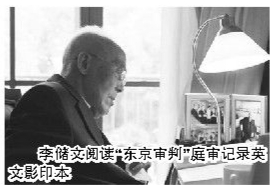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