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起床的时候,张延忠看到了这条手机微信。
“爸爸安详地走了,7月10日凌晨1∶10分。”发信人是叶静子,叶选宁的女儿。
张延忠是叶选宁的“发小”,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
此前,叶选宁已卧床多日,病危数次。
右臂卷入机器
1970年五六月间,身在湖南的叶剑英心急如焚,却无法到出事的叶选宁身边,只得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追问儿子手臂的伤势。
不久前,被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军队农场的叶选宁,往粉碎机里送杂草,不慎右臂卷入机器。当地医院勉强为他接上了胳膊,但机能几乎完全丧失。叶选宁决定去上海,再动一次手术。
当时,靠边站的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屋子里唯一可用的手摇式电话机质量不佳,他常常听得不甚清楚,请求接线员想想办法,减轻线路干扰,却被接线员没好气地呵斥一番。他挂了电话,双手发抖,满眼含泪,却也无可奈何。
1938年,叶选宁出生于香港。幼时的他没有见过父亲。那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正在国统区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一年后,因形势紧张,同样参加革命的妻子曾宪植将儿子送回湖南老家。
荷叶镇大坪村的大夫第是曾国荃造的,曾宪植是他的五世孙。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据说,大夫第是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重镇安庆之后,曾国荃带着掳来的金银财宝建造的。府第有九进十八厅,共148间房屋。
他在此间长大,被称为馨儿,后来读书、识字,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母亲住在全国妇联机关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暖气,用一个小蜂窝煤炉烧饭取暖。父亲已再娶,叶选宁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和妹妹,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住在北长安街上。他有时住父亲家,有时住母亲家,对父母都十分孝顺。
阿宁和老总
1959年,叶选宁和张延忠都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学中还有王若飞的独子王兴。10多年后,张延忠、王兴结为夫妻。
1956年,18岁的叶选宁参军。不久后,他被选入军委大连俄专,但因中苏关系紧张,最终没有去成苏联留学,于1958年转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导弹工程相关专业。第二年,张延忠、王兴也进入了这所学院。
那时的叶选宁喜欢音乐。有时,叶家父子会合奏一曲。叶剑英拉胡琴,叶选宁吹笛子,有观众的时候,就给大家表演一场,没观众的时候,父子俩自娱自乐。
1960年,因身体不好,叶选宁进入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他回到导弹部队,转战多地。
“文革”开始后,老干部们多多少少都受了冲击,孩子们放了羊。叶家如同开了流水席,被抄家的、没地方去的,十几号人挤了进来,隔两天又换一拨人,大多是叶家孩子小时候的玩伴。张延忠就住过叶家,也住过王震家。
叶选宁胳膊出事后,张延忠收到了他写的信。信写得并不凌乱,字迹清晰,她无法想象,这是叶选宁从三天的昏迷中醒来之后,用完好的左手写的第一封信。
叶选宁赴上海动第二次手术时,妻子赶到了上海,张延忠和王兴一同作陪。手术之后,叶选宁的胳膊接上了,但丧失了全部功能。他看起来并没有失落、低沉,不断问着其他人的近况。
练习书法
李卫平与叶选宁的相识,是1985年。那时,他在总政治部办公厅的秘书系统工作,叶选宁是总政治部联络部的负责人。1990年,李卫平调到这个部工作,担任秘书,受叶选宁的直接领导。之后的17年里,他的工作单位有过调整,但始终都在叶选宁的领导下工作。
叶选宁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用李卫平的话说:“他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叶选宁非常喜欢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副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当时曾国荃被削职,意志消沉,临别之际,曾国藩赠其对联,勉励他修身养性、再有作为。这副对联还是李卫平告诉叶选宁的,那是90年代初,叶选宁正处于事业的低谷。
叶选宁十分喜欢这句话,常常书写,送过李卫平,也悬于自己书画展的开头。
李卫平的事业遇到波折,叶选宁送了一幅字给他:“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不沉沦。”
这是鲁迅得知清末光复会成员范爱农醉酒落水去世的消息后写就的。原句说:“微醉自沉沦。”叶选宁把“自”改成了“不”。
叶选宁打小练书法,右手受伤10年之后,开始用左手练习。后来,他喜欢上草书,也喜欢隶书。写字见到好的、喜欢的,他都要抄写百遍以上,无论工作多繁重,每天都坚持。他的书法常落款为“雁洋叶三”。叶剑英是梅州雁洋人,叶选宁在叶家6个子女中排行第三。
李卫平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叶选宁去成都种牙,平时闲着没事,去了杜甫草堂。门口有个小伙子在卖字、刻章,叶选宁常去看,品评一番。后来,他和小伙子成了朋友。
他请小伙子给他刻了一个闲章,一直保存着。上书四个字,是他自己选定的:闲云野鹤。
(《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26期 徐天)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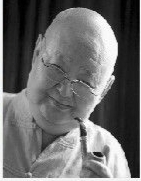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