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吕重华人生中,第一次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他自写自画的父子两代书店故事《订单》获得“世界最美的书”金奖,3月18日在德国颁奖。
书如其店
星期六上午刚一开门,一个小男孩就冲进门来买画纸,大石膏像后头,店里各式各样的美术纸堆得重重叠叠。暖烘烘的日头照进店里,黑底子绿漆的牌匾“方圆工艺美术社”字细方雅致。这是三十几年前父亲吕安未从《礼器碑》里摘的,吕重华亲手刻了牌匾。“我想做一家百年老店,这只是一个想法,只是愿意长期做下去而已。”
这个杂货铺一样满满登登的小书店里,他每天要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9点。他自己的书店里也有《订单》,《订单》里那些被装订起来的页码内容,都是吕重华多年向各出版社订书的真实订单。内容不是订书,就是向对方提出邮寄方式的建议。但奇特的是,每张订单后面,都有一个吕重华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时而大笑,时而发愣,时而怒气冲冲,时而泪流满面。看似信手而为,却与信件内容完全匹配。
书如其店。这本书既没有主线,也没有精彩绝伦的故事。正是书本身的设计,把书店的故事容纳了进来。《订单》的封皮是草绿色的编织袋,不是印在纸上,而是用真实的编织袋制作。“这书就是他这个人,就是他这家店。”书的设计师李瑾说。李瑾是吕重华在读西安美院设计专业时的同学。“我认识吕老板一家子,他们简直像卖菜,哪里像卖书。整天见他就是吃一碗烩面片儿,更不用提他穿的衣裳,几十年里就那么几件。”
“方圆”的诞生
吕重华的父亲吕安未开书店,实属“逼上梁山”。1957年,他离开山西农村老家,考入西安美术学院第一届油画系。1961年毕业后留在美院图书馆工作。到1982年,老家的妻子马秀莲带着两个儿子前来西安落户,吕安未第一次真切地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
吕安未除了画画,最熟悉的就是书了。他领到了西安雁塔区第二号个体户营业执照。一开始他挤公交车去进货背书回来,再由妻子背出去在学校门口、各美术班等地方打游击售卖,为读者找书、配书、寄卖书,还得经常送书上门。80年代人们的读书热情以及美术的复兴,使得这游击打出了名堂。弱小的“方圆”就靠着这样的起步,到1985年,终于在西安美院大门口,有了自己十几平方米的小店。
吕重华和哥哥自小在店里长大。他明明有进入西安高校做教师的机会,却要办书店子承父业。“我并不觉得卖书比大学老师档次低呀!”他和李瑾都对我说了一句话:“因为书结下的缘分,都是善缘。”哥哥吕秦兵自小因为打链霉素过量,造成听力下降,到西安后生活条件太差,逐渐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经过治疗有些好转,在卖书上能帮帮父母。我问吕重华是否考虑哥哥的情况才经营了书店,他说:“哥哥能上哪里去呢?书店还算是一个营生,起码让他吃上饭。”
老实人与老实书
吕重华对自己的职业认知很严肃,“我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书店,到第二代人来做这个事,那种还想精益求精、继续传承文化的精神,刚上手的人未必能明白。社会从耻于谈钱到恭喜发财,经历了很短的时间,然而对于书店来说,什么都没变。”
从父亲身体衰老到去世,书店受到房租冲击,吕重华觉得万把来张几尺厚的“订单”,可能是自己这辈子出书的唯一机会。他对于美术专业书阅读摸索多年,想做一本独一无二完美的书。
他在书缝线内部做成了四部小方块,每一部翻起来都独立成篇。正文内页则精选了有趣的订单,他写父母家人的文章,朋友们写他画他的,连同他最喜欢的瓦当、家人的创作照片和儿女的涂鸦都收藏在内。个人史的叙述也是他自己写的:“我没有雄心,出书也是很自私的初衷,想用家庭的细节,留下一点个人断代史。”
设计者李瑾在精神上认同吕家的书店,不是漂亮,而是一种“灰头土脸的与人相融”。很多年里,她对吕家书店遭遇的一切感同身受。她历数吕家母亲如何从健康到生病,吕家人的吃食穿着,到实体书店下滑和吕重华对未来的担忧。“这是老吕用生命做的一本书,也就这一本了。”
(《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2期 葛维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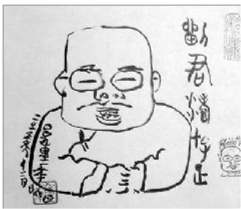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