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愿看到,城市人满为患,而身处城市的异乡人却有着“回不去的家乡”——
王君柏万没想到,自己一篇有感而发、略接地气的2015回乡散记,在微信朋友圈竟达到千万级的阅读与转发。他分析原因,“大概是激起了人们心底的乡愁吧”。太多人跟他一样,生活在城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留恋故乡。
意外之余,他觉得最有意义之处,在于这篇笔记,无意间成为他对最为崇敬的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105周年诞辰的致敬与纪念。
王君柏想,假若费老还在世,他一定欣慰,他笔下的农村样本——“江村”(苏州吴江七都镇开弦弓村),在中国发达地区的农村已成群出现;但他也一定焦虑,中国内地农村,远没有“江村”那份幸运,乐居富民不离乡的心愿被城市化的车轮碾压后,所见却是凋敝衰败、亟待重建的乡土。
有些东西,数十年前就被费老言中。费孝通在其被奉为中国人类学奠基之作的《江村经济》中写道:“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费老晚年也反复强调:“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愿看到,城市人满为患,而身处城市的异乡人却有着“回不去的家乡”,这,便是今天我们重提费老的用意。
老人与田地
老家村里一位80岁老妪自杀了,这对王君柏震动不小。她曾是村中风云人物,几个儿子又颇有出息,可老人无病无伤,偏要走绝路。
人不可能没来由地选择自我了断,这是促成王君柏今年暑假回乡看看的动因之一。他是湖南常德石门县人,现为无锡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心理学副教授。他读研时开始阅读《江村经济》,由此成为费老“粉丝”,今年又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得以进一步研究前辈思想的源与流,思考社会学的中国化之轨迹。今年7月,他回湖南老家,前后一周,每日与来访者闲聊,略作笔记,回无锡后便成一篇回乡散记。
令他感慨的是,访谈的对象中没有青壮年,大多是六七十岁老人,他们跟家乡的田地一样寂寥。
那些田地,远不及王君柏所工作的苏南来得吃香,“苏南一亩地,交给别人种,坐收千元,但放在我们湖南老家,苦于家中没有劳动力,只能无偿地交给别人种,而且是恳求别人帮忙。要想收租?那是天方夜谭”。
因为连插秧割稻的人手都捉襟见肘,老家的水田只能当旱地用,最普遍的是种玉米。过去要犁地、锄草,而今全以化肥、农药代替,导致土地板结、退化、产量大减。老人们实在有心无力,只剩自嘲:“这哪是种地啊?”
听父辈们感慨,30年前是村里最鼎盛时期,彼时,刚分产到户不久,村里132人,老中青搭配合理,青年占了一半。然而30年过去,村中现有人口仅剩当年三分之一。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当农村后继乏人,当老人看不到未来,当他们担心自己动不了时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他们中的有些人宁愿不活。
想必那位自杀的老妪便是如此。在农村,每一名子女都事先被分配好赡养老人之责,理论上,老太该由二儿子照顾。但二儿子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在农村,老太又不愿去儿子所在城市。那天,该是烧饭时间,对门的村民见老人家烟囱好久都没冒烟,推门一看,发现老人已自尽窗边。农村老人自杀已并非孤例,有学者统计,农村老人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甘蔗”和“混混”
聊天对象中一名尚显“年轻”的男子,是46岁的第一代进城务工者。
在王君柏看来,这是一位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打工潮北上南下,对农村尚有感情,于是一生积蓄,和大部分一代农民工一样,用来在家乡盖房。因买不起钢筋,只能求表面风光,用空心砖头搭建起的二层楼房,只要不发生地震,也是用来攀比的资本了。而今,他快要知天命,于是告老还乡,但他对土地,已远不及上一辈那般视若珍宝。想种点东西,发现劳心劳力,不由得心里要比较——同样的体力付出,在城里至少能挣回点钞票。于是忍不住又返回深圳打工。然而论体力、技术,他都不及年轻人,觅不到好活,只能当保安,或是大热天的帮人家看锅炉房。受不了这憋屈,他又回乡,如此反复,徘徊在家乡和继续打工之间,感觉两边都是鸡肋。
王君柏觉得,这正是“一代”的结局,“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城市,如一根甘蔗,被城市咀嚼并吞咽了甜汁后,只剩残渣”。
而“二代”与“一代”不同,他们直奔主题,完全以扎根城市为目的,却很可能希望落空。根据王君柏这些年来的观察了解,如今二三十岁的农村孩子,正面临“阶层固化”的困境——“真正能从农村走出来考上大学的,要比过去来得更困难。而步父母后尘外出打工的,则很难在城市找到真正体面赚钱的工作”。
于是,当立足城市梦破,当他们被迫在融入城市与退回乡村之间游离时,这个欠稳定且庞大的群体,便增加了一种可能——成为乡村与城乡结合部的“混混”。
给乡村机会
在丧失集体感、又在市场促进下不断“理性化”的农村,人心犹如一盘散沙。
散沙背后,人无敬畏,乡风良俗亦丧失了约束力。王君柏回乡所闻所见,一些十六七岁少女忽而私奔忽而又回,多次堕胎;夫妻间,不再相敬如宾、互有底线,因外出务工而天各一方的彼此,不愿再难为自己,于是各自凑对,难有自律;村中更常有年轻母亲,忍受不了贫困生活而离家出走,撇下不足一岁的孩子……
农村,难道真就这样,任其支离破碎吗?费孝通所主张的城乡平衡发展,难道唯有在沿海发达地区才能实现吗?是否,真应了经济学界的另一种观点:乡村的牺牲造就了城市繁荣,乡村最终的归宿就是走向城市吗?
但不可否认,内地农村所出现的城乡割裂,存在资源配置上的严重失衡,存在行政力量在城乡间的“厚此薄彼”,这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乡村逐渐被边缘化。
资源配置的“人为中心化”,还体现在乡村教育资源的撤并上。在许多农村,乡村学校被合并到县里,几十里上学路,家长们不得不到县里租房、陪读。而县里稍有地位、身份的人,又挖空心思将子女送往省城,如此层层向中心集中。王君柏曾就读湖南某县级中学,“我上中学时候,一个年级6个班,270人。而现在,每个年级招1500人以上。如此多的生源,证明乡村的学生数量远没有减少到需要乡村学校撤并的地步,反倒是地方政府有带动房地产业和县城消费的‘良苦用心’”。
所以王君柏热切呼吁,“给乡村机会!”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地方应尊重和关注乡村自下而上的需求,政府更应该助推鼓励,让在大城市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一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值得借鉴”。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国内已出现少数有识“乡贤”,自发回乡,再造故乡。全国返乡大学生论坛发起人陈统奎,是他家乡海口市博学村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他入学前,村民给他凑学费、办酒席,乡恩难忘。读书时,他多次写信给市领导,村里的用水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而今,他在工作多年后折返家乡,从事乡村生态重建和社区营造。他说,“要建有傲骨的美丽乡村”;数年前,浙江青田县36名华侨,纷纷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柬埔寨等地回国,在家乡当起芝麻村官,用自己经营企业和海外闯荡的经验、视野和资源来建设新农村;而在上海滩,第一位拿到上海“蓝印户口”的温州企业家邵联勤,于2011年回到了其老家樟岙村,“跨界”担任起村委会主任……
农村需要这样的优质乡贤,将一盘散沙重新凝聚起来,而支撑他们的,是剪不断的乡愁——农村,始终意味着人和人、人和食物、人和土地间的最美好关系。
(《解放日报》11.3 李晔)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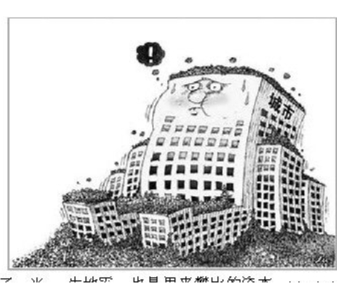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