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与治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多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起,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权威机构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13年的13年间,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发生了871起。
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2010年的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高达5517.7亿元。2011年、2012年则连续两年超过国防开支。
昆明“3·01”砍杀事件发生后,在成都和广州,数百名市民甚至因为一句“砍人了”的谣言吓得惊慌而逃。恶性公共安全事件已在人们心中固化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判断:在人群拥挤的公共场合并不安全。
为消弭社会的不安全感,公安部要求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截至2013年10月底,全国公安派出所警力达到55.6万人,较2012年底增加2.1万余人。2013年1至10月,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7%,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0.7%。一般而言,犯罪率低意味着社会安全感高。中国犯罪率的国际排名很低,但公众的感受却并不一致。
曾有人形象地称这类社会现象为“高压锅”,外表看起来比较平静,其实内部的压力很大。
目前全国约600个城市正建设“平安城市”,监控探头超过2000万个,投资超过3200亿元。但这似乎远远不够,除了警方监控,还有消防监控、城管监控等,都安装在城市各主次干道中;而大量私用监控的探头则被安装在小区内部、商场店家、公司企业中。
中国式焦虑
据中国疾控中心与北京回龙观医院调查,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这个数字,相当于西部省区一个小县的总人口。
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被媒体称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三大焦虑源。
焦虑感甚至威胁到家庭。中国每年451.6万对夫妻登记离婚,离婚率高达14.6%,意味着每天大约5000个家庭解体。虽然焦虑并不一定是离婚的唯一原因,但心理学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对家庭的影响已不容小觑。
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年轻人都喜欢把“压力山大”“郁闷”作为口头禅,无奈的背后是深陷焦虑中的自嘲。有统计表明,不管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蚁族”,还是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焦虑。
富裕阶层安全感要好些吗?答案是不尽然。一项针对全国150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研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勉强“及格”,“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是造成企业家不安全感最主要的根源。《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显示,企业家犯罪集中在民营企业家身上,从最初的与国营企业家基本持平(2009年,35:49),到目前数倍于后者(2013年,87:270),这表明民营企业家在这五年里日子并不好过,主要集中在融资、财务两大领域。
“橄榄型”社会在哪里
中产意味着生活富足且稳定,有足够的时间度假,代表主流社会价值与秩序。中国官方2004年曾有标准:人均年收入2万元,即户均收人6万元以上,即是中等收入,当时约有20%的群体达到这个标准。颇具讽刺的是,北京当时购买经适房的收入标准与此标准几乎一样。
“中产”在中国是个争议话题,无论多么权威的机构发布的报告,总会引发质疑和吐槽。国际货币组织(IMF)的专家认为,虽然中产是那些月收入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人,但这一收入事实上根本无法在北京和上海这类大城市享受中产生活。
一套房子拖垮一个“中产”成为不争的事实。本来经过多年打拼的白领正在筑垒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但飞涨的房价让他们的“中产”梦碎。一项调查显示,上海70%以上的白领还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中38%患有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等运动系统疾病,32%存在肠胃、肝脏等消化系统问题,22%有失眠、抑郁等心理疾患症状。如此白领,与“中产”的外在与内在生活要求相去甚远。
在社会学家眼中,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只有壮大这个群体,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才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已过半,但就现状而言,中国农民不可能短期成长为中产阶层。最有潜力迈入“中产”门槛的城市白领处境堪忧,而作为中产预备力量的大学毕业生也中途遇阻,照此下去,中产阶层的新生力量后继乏力。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0期 席志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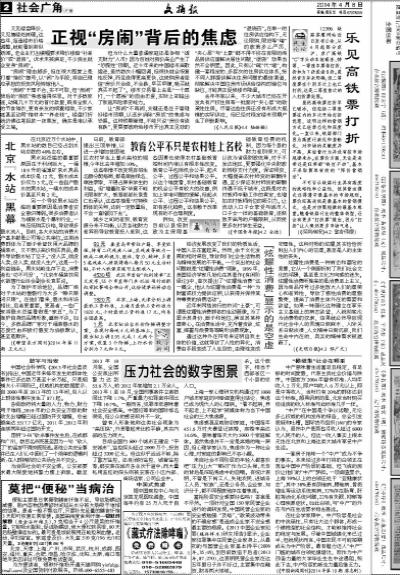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