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曾以“要求忏悔是克隆‘文革’吗?”的通栏标题发表了两篇观点看似对立的文章:徐友渔《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和于坚《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不管双方的立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忏悔”一词不言而喻的自明性。似乎“忏悔”就像“检讨”、“自我批评”一样。
当真如此吗?
“忏悔”一词究竟要用在什么语境中?是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是儒家无神信仰的良心语境,还是现代信仰危机诉求的道德自律与交往规范的共契语境?此外,还要弄清楚“忏悔”的范畴及其属性,一般忏悔只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同道德相关。它显然不应属于界定“罪”与“罚”的法律范畴,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即可;只有在法律不到的地方,道德才起作用。确定这两点很重要,不然,讨论既没有可参照的前提,也没有可通用的概念,结果只能是你打你的锣,我吹我的号。
一些人口中或笔下的“忏悔”,多半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混合概念,虽然以现实的道德关怀为主,但它最初震惊的却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素有“道德渊薮”之称的国家和人民为何今天道德如此贫乏,以致“文革”及其后续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恶行,从来没有谁出来自责检讨,更遑论勃兰特式的沉重一跪,除了上行下效的推委搪塞文过饰非别无其他。
我认为徐、于二人的文章并不对立。他们各自立论的角度与层次并不相同,宁可说他们是互补的:“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忏悔”恰恰是“个人自由”的表现。换句话说,忏悔本是解脱罪感的自由行为,即自由意志的自律。
拿“文革”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比附“忏悔要求”与“忏悔”,已经是概念的转换造成问题的误导。似乎在这种“批判”式的“忏悔要求”面前,今天就应该伸张忏悔不忏悔完全是个人自由的权利,就像宗教信仰也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一样。谁强迫谁就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克隆“文革”。如果我是有罪的人,我不愿意别人强迫我忏悔,特别是不愿意别人用他自以为是的“真理”作为我忏悔的标准,这时,我可以抵制他说,“忏悔是我个人的自由,我有不信仰你的真理的权利”。当然,除了我有罪过,我还是个没有信仰、不要信仰的政治实用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或平庸主义者,与忏悔无缘也并非不可。但是,一个人可以这样,无关宏旨;一个良心、一个民族也都这样,就像沙暴弥漫京城,危机可就大了。顺便插一句,今天瞎子也能看见,人自身的“自然生态”的破坏同外部自然生态的破坏一样,都到了大危机的程度。
“忏悔是个人的自由”,表达和理解起来,可以分外拒与内启:“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不用你管”(外拒);“忏悔是个人的自由,忏不忏悔恰是个人自不自由的一种获得”(内启)。于文只取其一而不取其二。可见 “外拒”常常是“内启”的遮蔽形式或自欺形式,特别是对防范过度或逆反过强的人,成为情结。“文革”后的中国人,大都吸取了这个不成文的经验教训以“自卫”,结果是,不仅人际关系隔膜与紧张,个人也闭塞了深入开拓以道德自律的进路。
忏悔不是法律强制下的悔过自新,它必须是自己内心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认罪涤罪的解脱,还要表现为德行的增进。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不完全是私人密室中的话语,说说就算的,它要诉诸意志和行为,即便不是或不能当下兑现的弥补,也要更新或改善自己德行的承诺。另一面,忏悔要以宽恕他人作为请求宽恕自己的同等保证,所以两者的亲和性是以“爱”生为目的的。
没有“罪感”是谈不上“忏悔”的。而忏悔中的“罪”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可以是一般的过失在忏悔中升华的“罪感”,也可以是丝毫不轻于法律的“罪行”,只是因种种原因未诉诸法庭追究而已。但不论何种“罪”,非要在赎罪的承诺中以求达到救赎。若不如此,说说就算,无异于自欺欺人。所以,对一般人而言,关键不在于非公开说出来以“表示”忏悔,而在于自觉德行的开启与践履。
总而言之,“忏悔”虽在个人之中,但一定要在个人之上获得超个人的审视的眼光。否则,连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在“忏悔”,更不会知道“忏悔”为何物。所以,真正的“忏悔”,即便你不说出来,你仍然相信自己被公认的他在审视着,既不能欺骗也不能冒犯的。正因为如此,有“真理”的理性主义者和无信仰的虚无主义者一样,都不会“忏悔”,也无法“忏悔”。
中国人虽不信仰超验的“神”,也不真信仰形而上的“普遍原则”,“良知”或“良心”还是相信的,所谓“天道”也只在“良知、良心”的“人伦”化基础上被相信着。日常用语 “凭良心”,可以作为“忏悔”的依据,但只能起着“弱作用”,因为在复杂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环境中,“良心”、“人心”很容易滑向“个人之心”,不一定是你有意为之,而是你无法分辨。这也是我们“忏悔意识”弱而“实用意识”强的原因。
今天即便因具体的道德危机而需要“忏悔”,也决不能简单启用传统的“忏悔”形式,或动用基督教的“救赎”,以为读几遍《圣经》就能“忏悔”了,或动用儒教的“良知”,学一个孔夫子的“我欲忏悔斯忏悔至矣”,没那么方便的事。除了我们每个人拖着有罪的历史,现实中还塞满了假正经的观念、生存攸关的利害以及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对于没有忏悔“习惯”、没有忏悔“氛围”的我们,即使你想忏悔,也未必忏悔得了的。
我可以借“文革”一例稍作演示。
王是我在“文革”中结识的朋友。1985年,王偏瘫了。他极度懊伤。我把他接到家中住了半月,想在交谈中劝慰他。他说了一件事。
1968年春,晚上九点多钟,我同“二司”的小魏去看刚从北京回来的老宋。谈得正欢,突然闯进来五个人。两个站在门口,两个把老宋带进里房,一个自我介绍并检查我和小魏的证件。我当时的身份是“市工代筹”代表,小魏是武邮学生但证件是《长江日报》记者。我站起来大声说:“老宋,我和小魏先走了。”说完就带着小魏向门口走。两个人想拦住,被检查者制止:“让他们走吧。”
第二天我去看老宋,他爱人说昨晚他们是来抄家抓人的,“当时你不该走,你可以阻拦他们。”我说了我不能不走的原因,“小魏不能牵扯进去。”
四个月后,老宋跳楼逃跑摔断了腿,又被斗得死去活来,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我去看他,说:“我不该走的。”他摇了摇头:“没用。”不久,老宋死了。1983年平反,才弄清楚,仅仅因为老宋去了北京,怀疑他参加了“北航黑会”。
这件事一直卡在我的心里。我当时离开,表面是为了小魏,实际上是我害怕了。而且这种怕,还不是怕牵扯到“工代筹”中去不利于我和组织的处境,小魏和老宋当时都是“神秘人物”。这怕,几乎纯粹是当下生理性的。我弄不明白,我这个人内心怎么这么胆小。结果,老宋死了,我也关起来。在劫难逃。关在里面,我才发觉,真正使我难受的,是老宋的死。不管我的阻拦有没有用,我做了,今天就不会后悔;不做,怕,无论对朋友对自己,脱不干净的是卑鄙、胆小、自私,甚至,老宋的死,也有我的出卖、推卸或逃避……
老宋的爱人和孩子后来见了我都客客气气。我知道,她们不说,心里是怨我的。我也怕见她们。直到我发病了,她们一家才来看我,我反倒很坦然,报应把我们扯平了。
王给我们提供的无疑是一个认真“忏悔”的形象。这种事在“文革”中太司空见惯了,换其他人,可能算不了什么。他和宋的私交并不是很深,也没有特别的派性关系,他完全可以不如此承担责任的。但王却看得很重,因为这件事确实触动了他内心深藏着的怕,而表面上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沉着无畏的。
作为现代中国人,王能“忏悔”到这个分上,已属不易。但仔细想起来,它算什么类型的“忏悔”呢?一片混杂,但却真实。
1986年,王也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允许我引证一些我们当时谈话的内容。
“如果你不被关,如果你不发病,它仍然有这么重的分量吗?”
“会是一件事,但可能就压在心底了。平时忙起来也顾不上它。”
“这么说,你是在‘劫数’、‘报应’的启示下才有更深的忏悔的?”
“可能是吧。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有时间、才有契机进入最内心的反省……啊呀,你逼着我正视一个事实,你肯定早想到了,你认为我是在功利心的驱使下忏悔的?”
“没有,真的没有。”
“不要骗我。或许我真的是这样。我是为了我的病好,就像我四处求医求药,我也在内心翻遍自己的罪过,检讨、忏悔,许愿,乞求宽恕。我把忏悔当作与冥冥者交换的礼品了。”
“我真的没这么想。我只是从你的用语中感到了某种我不能确定的倾向。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相信‘劫数报应’,还是一般说说。”
“是很糟糕。一场病把我变了,变得迷信。即便我信神,也是完全实用的目的,为了把病治好。要是病真治好了,我可能信神,也可能不信神,多半不信神。糟糕就在这里。”
“我关心的仍然是,你对老宋的死有很深的内疚,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只会从老宋的死引申出社会批判,当时是派性批判,今天是‘文革’批判,或许它是掩藏或转移内疚的最好办法,自欺就是这么完成的。而你却敢于承担罪责。许多问题上,你和我的取向常常有这种外向内向的差别。所以你写小说,我做社会学。”
“别用损自己的办法安慰我。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的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一站起来我就感到了,我知道我是因为怕才站起来要走的。虽然也意识到带走小魏的理由。第二天去看老宋已有预感,已有愧疚,只是不承认罢了。后来老宋出了事,最后死了,内疚才一步一步变成摆脱不掉的罪责。”
“你是说,它最初就在一种直觉中,无须借什么理论反省的。”
“怕,我怕了,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不仅在场,而且出场了,这是自己无法骗自己的。要装正经也是后来的事。”
“可能你太敏感了。有的人,比如我,训练有素的意识常常会成为本能情绪的合理武装。我的反省总是事后特别是遭受了挫折才开始的。要忏悔,恐怕还得先用理论解除理论,即解除我已习惯了的意识武装,就像‘文革’中的人必须剥掉‘文革’的武装一样;还不够,还得借一种眼光,才能看清自己的罪。我不知道这种眼光,单凭良知够不够?历史上最讲良知的王守仁,杀起农民军来从不眨眼的;现实中,为了革命的利益,饿死再多的人,也损害不了伟大本质的一根毫毛。本质或真理,要在曲折中前进,有时免不了牺牲,甚至无辜的牺牲,难道能因此牺牲而葬送或放弃革命的理想吗?你看,良知的小道理要服从历史必然性的大道理。许多事情,恐怕是良知直观不了的,就像康德的‘崇高’是知性直观不了的一样。所以今天才迫切需要一个任务,那就是,撕掉真理的面具。”
“结果是再换一个真理,换的总是最好的。”
“那就清算真理本身。”
“不要真理,如何知道是非好坏善恶?如何知罪改邪归正?”
“不是不要真理,只是不要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独断形式。有两难,才有另类选择。不然就会永远重复下去。”
(摘自《幽僻处可有人行? 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1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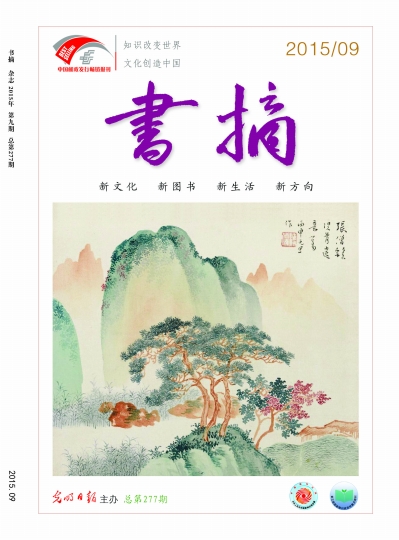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