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南,人才辈出,仅王氏一姓,便涌现出衡阳王船山、宁乡王九溪、湘潭王闿运、长沙王先谦四大家。其中,尤以王闿运最具特色。他不仅满腹经纶,且狂傲不羁,堪称晚清士人中之一“异类”。
王闿运之“狂”,其一在于他恃才傲物,睥睨群伦。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拿下金陵,重开江南乡试,一时间江南学子们纷至沓来。战后之六朝古都,一片萧索残破,加之湘军军纪不佳,招致不少士人不满,他们甚至迁怒于湖湘子弟,笑他们粗俗无才。此话传至王闿运耳中,令他颇感不平,遂写下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濂溪指湖南理学先贤周敦颐,王尊其为儒学正统,自然将那一班江南士子归为“湘学”余支。该联写得诙谐、大气,王闿运那股子“狂劲”可见一斑。
王闿运之“狂”,其二在于他自诩霸才,语出惊人。他专研帝王之术(帝王之术,顾名思义,即教授君主如何驾驭群臣,或指点权臣怎样挟帝王以令众僚,以实现篡权之野心,又称“纵横术”),渴望有朝一日能施展其平生所学。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已手握苏、皖、赣三省军政大权,成为清廷倚重的“红人”。王闿运风尘仆仆,来到湘军帐下,欲图向曾兜售其帝王学。
初次见面,王暗示曾道:“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此中深意,明眼人一望便知。在王看来,曾国藩之道德文章,若想超越“文宗”韩愈而直追西汉诸贤,难上加难,尚需数十年沉潜修炼;但要是效仿蜀之孔明、魏之曹操,独揽大权,翻云覆雨,改朝易代,则仅用三五载即可。而曾国藩却故作木讷,毫无反应。
之后,王又与曾长谈达13次之多。一日,王将话挑明:“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话音刚落,曾将脸色一沉,借故出去。于是王走到曾书案前,发现其在所批公文上写满“妄”、“谬”二字。至此,王顿觉帝王之术已作泡影,无可挽回,徒叹“贤豪尽无命,天意悲难凭”。
其实,曾国藩对王之游说并非无动于衷。他曾在日记中记道:“傍夕与王壬秋(王闿运字壬秋)久谈,夜不成寐。”想必王之狂言也令曾一度心潮澎湃。要不,他何至于通宵失眠呢?只可惜,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
王闿运之“狂”,其三在于他不惧淫威,巧言戏谑。民国肇造,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欲复辟称帝。他想借重王闿运之名望,故聘其担任总统顾问。王早已识破袁之把戏,于是撰联一对加以讽刺:
顾我则笑,
问道于盲。
后袁一再催逼,不得已,王出任国史馆长。不过他讨袁之反感有增无减,甚至于国史馆门上手书对联一副:
民尤是也,国尤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旁观者清”。嬉笑怒骂,皆寓于联中,实乃近代对联经典之作。此老翁似是意犹未尽,还曾撰联一副: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联内藏话,弦外有音,其警告袁世凯勿逆潮流而动之意溢于言表。
晚年之王闿运一直对其帝王之术无处施展之事耿耿于怀,他在自撰挽联中写道:
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好一个“空”字,诉出了多少无奈与沮丧?然而,时至封建末世,帝王之术已是明日黄花,沦为背时之学。在中国走向共和之际,像王闿运这样的末代士人便也只能“空留高咏满江山”了……
(摘自《杂拌儿民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3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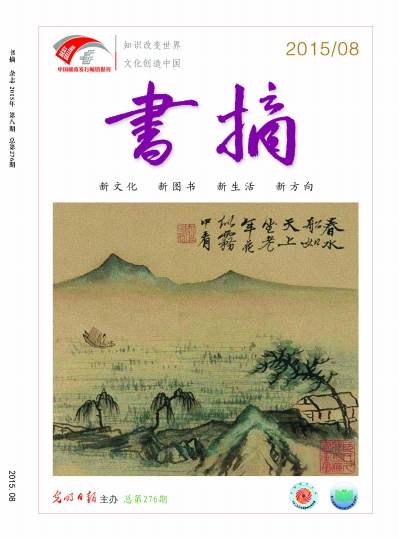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