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的下午三时,J依约而至。
其实,是女儿的发想,想趁J尚未赴欧洲旅游前,再邀她到家中来喝一杯亲自调制的Cappuccino,聊表我们对她的感激之情。
J是丈夫的家庭访问护士。数月以来,每周固定到家里来,为生病的丈夫做例行检查、打针、打点滴等等。我们似乎已经超越一般病患的家属与访问护士的关系,自自然然成为异国的朋友了。
她径自在厨房里熟悉的便餐桌旁坐下来。厨房里的便餐桌比餐厅饶富亲切温暖的氛围。过去,有些不便在病人前谈说的话题,我总是请J在这张圆桌前坐下来悄声交谈。
“你们要跟我谈什么话呢?那张沙发椅上不见你先生,有点儿不习惯。”J把视线移向客厅的方向说。
岂止不习惯,简直是梦一般。
数月来昼间总是躺在那里,状况好时甚至坐在那里的人,说走就走了,留下一张空虚的沙发。心中顿时一紧,眼中也发热。
J选了一个面向阳台,看得见蓝天和青山的位置。
五十五岁的她,虽然短发已经华白,壮硕的身子却十分硬朗。作为一位退休的护士,她继续担任访问护士的工作,从早到晚驾驶一辆旧车,遍访附近有重症病患的家庭。她曾对我说过:她爱这份工作,远胜于以前在医院的护理职务;因为走入患者的家庭,使她接触到更多的人性层面。
“今天,我们是纯粹基于友谊,邀请你来喝一杯咖啡。不谈我的先生。”我极力装得寻常平静的模样说,“何况,你就要远赴欧洲去旅行了。我们将有一段时间看不到你。”忽然被自己说出口的话触动,对J的即将远行,竟十分依依起来。大概我已经习惯每隔若干天就见到她来,带着温度计、听筒或针管什么的来看顾丈夫;她的来访总给我一种安全感,好像丈夫的病就会因为她的来临而逐渐好转甚至痊愈。
女儿在便餐桌旁的窗台上专注地调制Cappuccino。屋内弥漫浓郁的咖啡香。
“给你一杯特大的吧。放假日子,你看起来反而累一些的样子。”
女儿善体人意,递给J一杯容量加倍的白瓷咖啡杯。J把大型的咖啡杯慎重地用双手端起放在鼻下,略略嗅闻,十分欣赏的样子。
和女儿说好在J远游之前的今天,我们要避开伤情的话题,究竟对一位不为看护来访的护士应该谈些什么才恰当呢?
一时间,交谈中断,留出一片空白。三人默默地啜饮着各自的Cappuccino。
“我的女儿,利用回来照料她父亲的机会,到她的母校选修夜课,学习金工了。”
忽然,想出一个转移伤情的话题。于是,女儿取出她自己设计的一些作品,摊放在桌面,谈话的气氛果然就稍稍明亮起来。
“哦,这些真的都是你的作品吗?”“多么有创意,多么好看!”J一一仔细地欣赏着女儿的金工作品,甚至捡起试戴在手指上。
“多么有创意。”J重复道,“有其父必有其女。你们真的是一个艺术的家庭。”她看着手指上的戒指,又抬眼望墙上挂着的丈夫的画作。
我的心底,骤然遂生一种抽痛的感觉。或许,J和女儿也都有类似的感觉吧。几度抑制讳避,谈话的内容终究还是回到离去的人。
“前天晚上,我还梦见你先生呢。”
“其实,你不应该牵涉太深的。”
“是。我知道的。我太不像一个专业的护士了。”说着,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四周竟然红晕湿润起来。
1
第一次看到J的眼眶发红,是在她来访未久的一个早晨。为丈夫测量体温、血压和打针等等例行工作完毕后,见他削瘦的身体埋坐沙发椅内,面色苍白而凝重,J忽然停止收拾携带的护理工作包,又回到她经常坐的小椅上,握住丈夫的手,温柔地问:
“你在想什么?告诉我,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知道这许久以来,你心中一定很苦闷。很多事情,你想做,又没法子去做,是不是?”
因为久病而羸弱的丈夫,似被J一语道破心事,尽失往昔爽朗的性格,变得异常脆弱,泪水在眼眶转动,声音颤抖着说:
“身为一个男人,在走之前,我应该对这个家和家人有所交代才对。每天晚上,我都希望次日醒来可以精神好些,做一点事情;可是,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体仍旧很虚弱,没法做我脑子里所想的事情……”
J像慈母一般拥着丈夫单薄的肩头,泪水潸然。丈夫极力坚持着的男人的尊严,遂终于不可克制地溃崩,双颊尽湿。
“你细心照料我,又为我向保险公司争取高单位营养剂。你为我所做的种种,我不知道如何报答。”丈夫说到这里,甚至哽咽,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只能铭记在这里……”
一时无语,三人都落泪。J把几上的面纸抽出,递给丈夫和我,自己也不断在擦拭。
那天J离开时,丈夫破例地扶着助行器送她到门口。对于羸弱乏力的病人而言,大概那是表现感激之情的唯一方式吧。
数日后的夜晚,丈夫的血压偏低至危险的警戒线,药房临时送来生理盐水,但是当时的我和女儿都尚未谙操作方式,只好打电话求救于J。从微暗的下午八点半,到漆黑无月光的午夜,盐水一点一滴以设计好的缓慢速度流入丈夫的静脉内。J在等待结束的三个小时,便借用邻室餐桌,整理她日间访问的许多病历报告。
超过十二小时的工作,令她疲惫已极。见她时时揉眼,哈欠不禁,我沏了一壶热茶放在她面前,她微笑着端起茶杯说:
“我很好。这是我的工作呀。呣,这茶好香!”
点滴结束,丈夫的血压回升。J终于结束一整天长长的工作。我陪她步出微寒的门外。拾阶而上时,她几度回首对我说:
“你别跟我上去了。快去陪陪你先生吧,他需要你。”
但我内心充满感激,坚持要送到车停之处。在J打开车厢盖子时,我忽然觉得孤立无援,便央求:
“我们可以见见面、聊一聊吗?”
“现在吗?要谈你先生的病?”她在昏黄的路灯下,狐疑不解地望入我的眼眸问。
“不是,在你方便的时候。我很需要一个朋友。”说这话时,我几乎要哭出来。
2
几天之后的黄昏时分,我到J的家,其实,我只是要选择自宅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和她静谈。我们两个人提议了若干地点,但是咖啡馆和餐厅都不适合当时的处境心情,最后,J才邀请我到她的家。“我常去你们家,为什么你不到我那儿来坐坐呀。”她的语气十分诚恳。其实,J的住处与我家相距约为车程六七分钟,可谓近邻。J笑着开启矮门让我进去。“哎呀,你穿得那么整齐,看我这一身邋遢相!下了班,在院子里浇水呢。进来,进来。”
她穿着无领无袖背心型线衫和一条短裤,并且光着脚,露出晒过太阳的健康肤色。美国人居家模样便是如此随性。
显然,她原来就在院子的野餐椅上喝着红酒。一把大型的遮阳伞,挡住了倾斜的夕照残晖。
我落席在旁边的木椅上。酒和茶和水都不要。我刚刚在家吃过晚饭出来的。J也不勉强,她推了另一只木椅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你有什么心事吗?想跟我讲什么?”
被这样单刀直入地问,倒是很难以说明当时的心绪。老实说,也并非有什么特殊的事件或心思想要告知她,只是许多时日以来面对着不可预知的丈夫的病,令我感受莫大的压力与焦虑。我需要一个朋友,一个不是寻常朋友,而是完全了解我身心处境的,像J这样的人,与我谈谈。
然而,面对着J,在吹着微风的院子里,我仿佛心中便升起一丝温暖,觉得不谈什么也可以。于是,J喝着杯中剩余的酒,我们漫谈着一些琐细的事物和人情。
“我可以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事情吗?”在谈话告一段落时,我有些好奇地问J。
“你很少提到你的先生,而且常常使用过去式。请问他是……”
或许,这个问题太鲁莽,我有些后悔起来。但是,J在稍微停顿了一下之后,倒是很坦然真诚地回答我。
“哦,我们离婚了。”她像一个思维清晰的人说话的方式,先把大轮廓提出来;接着补充说:“离婚几年了?很久很久,我一下子记不得了呢。”尔后,忽然大笑起来,令我更加后悔。
“对不起。请原谅我鲁莽。”我嗫嚅而道,希望结束可能引起她感伤或不愉快的话题。可是,J在笑完后,仰首饮尽高脚杯中残留的红酒,要把话继续说下去。
“他在我生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后,没有多久,向我提出离婚的要求。当时,给我的打击很大。他说:爱上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竟是我的好朋友!我完全不知情。他是一个好人。我们过着寻常平凡但是幸福的生活……至少,我认为是幸福的生活……”许是触及尘封已久的伤心事,J的声音有别于平时的温柔,显得相当激越。
“不要谈吧。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问你的。”我轻拍J的肩头,想平抚她激越的情绪。但她回望我,带一丝苦笑说:
“没有关系的。这许多年以来,我始终没有好好向人叙述过。平时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回顾……或许,是我故意让自己很忙,免得回顾太伤心;不过,实际上我也真的不得不忙碌,以维持生活。
“我答应我先生离婚,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四个小孩,一儿三女的监护权都归我。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自己必须要争取到这一点才甘心。那是很有骨气的抉择,但也是极困难的实践啊。虽然我接受前夫所付的赡养费,可四个孩子的养育问题,比我想象得困难得多了。”夕阳最后的璀璨把J满面的泪痕照射得剔透。
“你从比较年轻时就做访问护士吗?”我想也许岔开话题,可以转变J的情绪。
“不,我原先是一家大医院的护士。我大学时代,其实是很喜欢文学的,像你,像我的先生。
“我和我先生就是在大学里相识。他攻读文学和哲学,对人生有浪漫的憧憬。便是受他的影响,我婚后还上研究所,读护理哲学。所以我对于病人的关怀,不只是在于他们生理方面的疾病,更注意他们的心理以及处境、文化背景等等因素。
“生了孩子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没法子工作。离婚后,我把孩子们送去托儿所,重新又回去工作,一直到四年前退休。曾经在家休息了一阵。可是,孩子们都长大了,最小的女儿也入大学,我就复出,接了这一份家庭访问的护理工作。咳,好长的人生啊!”J耸了耸肩,笑一笑。眼中犹有泪水。
“我爱现在的工作。比起在冰冷的医院,走入病患的家庭,我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生活、人性、文化,使我有机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
西照渐渐转弱,暮霭已在不知不觉中包围了J在半山腰的屋舍和院落,颇有些凉意。我已经看不太清她是否仍在流泪,只觉得声音似已恢复平静了。
稍顷,J伸出手握住我搁在木桌上的右手,试图在暮霭中分辨我的表情,带些腼腆的语气说:
“啊,说了半天,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来找我,原来应该是有什么话对我说,我来听你的才对。你看我,真难为情,还哭成这样!”
天色已暗,我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谈话内容,却意外地听到J的故事,令我明白在明朗温暖的背后,其实正隐藏着这许多辛酸的泪水。
我起身告辞,说:“下次再告诉你吧,我的心事。”
3
然而,并没有下一次。
丈夫的病况急转直下。在医院的加护病房住了十天后,没有丝毫起色。
“如果最后的时刻到了,不要让我太痛苦,太没有尊严。”得悉罹患重症后,丈夫曾嘱咐过。我没有忘记。
征得主治医师同意,我们选择了把他带回家,给他消极的治疗及积极的止痛。我们向院方央请三位访问护士中,一定要包括J。
轮及J来访那天,因有事,她要把原定上午的时间改为下午。午后三时,她准时按门铃。
J进了房间,为昏睡的丈夫量血压、测脉搏。血压低、脉搏弱,不是好的现象。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J严肃地同我们说,“千万要打电话给我,即使是半夜也没关系。我就住在你们家附近的。”
J几度提起医疗箱要走,终因雨势太大,不得不又留下。
屋内除病床上的丈夫外,J、儿子、女儿和我都在床边轻声交谈。更轻的是收音机播出的乐声。是儿子的想法,把客厅中的大型收音机搬入卧房,让好听的音乐陪伴着父亲。
“听,你们听。这是我以前常常弹的古典吉他曲子。爸爸最爱听的。这简直就像是广播电台替我弹奏给爸爸听哩!”儿子感动而兴奋地说。
“我年轻时候,也喜欢弹吉他。你们知道,就是在越战那个年代……”J向我们谈起有关音乐的回忆。一时不急于离去的样子。
女儿绕到她父亲面孔朝向的一方。忽然说:“奇怪,爸爸的呼吸好像变得很弱了,有时停止一下……”
我们都起身过去。
丈夫的呼吸果然变得很虚弱。虚弱、停止。虚弱、停止。虚弱、停止——
J用三只手指按着丈夫颈边的脉搏,宣布:“他过去了。”然后,看看手表,告诉我们:“四时十八分。”
(摘自《人物速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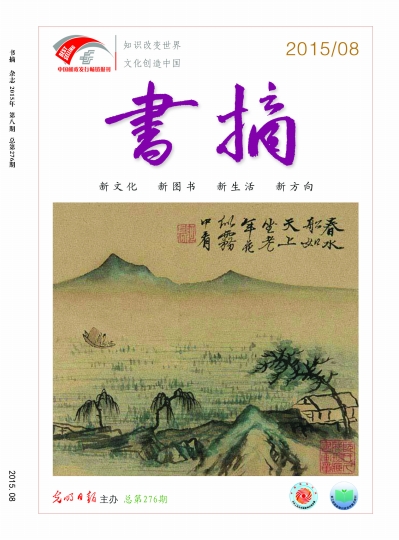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