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有的真讲学问,如康熙;有的虽然纨绔,但至少练得一手好字,出外题字不致太露马脚,如乾隆,如同治。满清皇帝的学问,好过明朝的草包皇帝,这是真的。但是,皇帝讲学问也带来新问题。以前是朱熹、王阳明这等的大儒才有资格讲“圣学”。康熙以后,皇帝亲自过问学术,只有皇帝语录,皇族意识形态才有资格被称为“圣学”。“圣旨”代为学术,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现象。皇帝带头学外文,也被包括为清朝“圣学”的一部分。清朝皇帝哇哩哇啦学外文,成了紫禁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清朝皇帝学汉语,也是讲“外文”,但这里讲的外语,确实是欧洲语言文字。西方文献记载,康熙和张诚、白晋等法国耶稣会士关系很好,曾经学过法文。但此事在中方资料不见记载。康熙曾经关心过清朝的拉丁语、俄语教学,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语言学造诣,此事史有明载。据《大清圣主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俄罗斯贸易代表团向中国政府递呈文书,平时学问满坑满谷的大学士们居然不能翻译,只得将原文进呈。康熙皇帝凭他与法国人交往得到的欧洲语言知识,教导汉员说:“此乃拉提诺托、多乌祖克、俄罗斯三种文字也。外国文字有二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上去声,而尚有入声。其合字合意甚明。中国平上去入四韵极精。两字合音,不甚紧要,是以学之少,渐至弃之。问翰林院四声,无不知者。问两字合声,则不能知。中国所有之字,外国尚知之。特不全耳。此后,翰林院宜学习外国文字。”
康熙的外文水平到底如何,现在无法考证。当时还没有字典,也没有教材,康熙肯定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外语训练,但是他至少一鳞半爪地学了不少单词。白晋写《康熙帝传》,其中有说比利时神父南怀仁陪康熙打猎,“皇帝问他,这种鸟用法兰达斯语怎样称呼?南怀仁神父几年前曾对皇帝讲过。但这鸟相当罕见,有点忘了本族语言的神父怎样也想不起来。皇帝马上问他,不是如此称呼吗?神父十分惊奇,因为康熙竟还记得他自己都已忘记的东西”。南怀仁是康熙的好朋友,讲的是佛兰德语,是接近荷兰语的一种方言。
康熙学外文的动力,主要来自学习欧洲天文、地理、历算的兴趣。这是主动好学。但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目的,就很被动了。那是被欧洲人打怕了,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1892年,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万国公报》上报道光绪皇帝亲自带头学英语。“前阅西报,敬悉皇上于几余之暇,召取同文馆士人讲习英文。欲将英国文字语言贯通熟习,以裕圣学,俾他日中西交涉得有操持”。外国人听皇帝口吐ABC,喜不自胜,英国《泰晤士报》有特别报道。李提摩太更认为这是“振兴中华”的开始:“此在中西明理之人同深庆幸,未始非中国振兴之转机也。”所谓“一言兴邦”,又有新解。
其实,光绪表率英语教学实属无奈。早在1862年,北京就建立了京师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挑学生学英语。当时没人愿意来学,结果来了“四十个老青年”,都是科场屡试屡败,实在没法吃到官俸,不得已来混差的。一天,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在街上撞见自己的学生,带着孩子。问道:“这是令郎吗?”回答竟是:“不,是我的小孙子。”没人肯好好地学外语,光绪只能自己带头学。
据丁韪良的回忆,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是他的同文馆里的两位毕业生。英文水平本来就差,课文都是丁韪良帮他们拟好。加上皇帝金口玉律,说错了,老师也不敢纠正,只能听任其错。这样如何学得好。光绪每天被授课半小时,但不知什么缘故,他要在早上四点学英语。师生们半夜引吭高歌,大约又是引得老佛爷生气的原因之一。
光绪学英语的那一年,宫中一时有许多人也来赶皇帝的时髦,亲王大臣在京内到处请老师。见面时Good Morning,道别是Good Bye。光绪皇帝一年闭门造车,春节时准备了一份英文的演讲稿,兴致勃勃地向各国公使演讲。但不知为何,那天各国公使到得不齐,恐怕皇帝的英语也实在不能恭维,没有得到好评。皇帝大丢面子,从此学习热情一落千丈。按传教士的逻辑,中国没有振兴成功,或许也应归因于这次考试失败。
其实,皇帝的外语好不好,与国家强不强没有多大关系。西哈努克亲王的法语讲得和法国人一样好,柬埔寨照样的弱。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没有学会英语,但维新终于成功。皇帝自作表率,学讲外文,推动“开放”固然是好,但口头开放,不及心头开放。康熙学外文的目的含着一些好奇,但主要还是向满汉群臣炫耀自己的“圣学高明”。光绪学外语,那就是一种“不得已”,并不是真的要向域外求索新知。光绪学英文,实在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老佛爷、洋务派和颟顸官吏看看而已。
(摘自《历史活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2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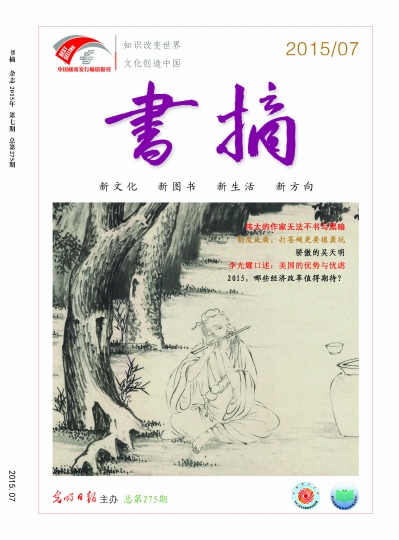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