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到我从前的村庄,发现曾经树木葱郁的青山已变得光秃,除了满目的野荆和裸露的山岩,已听不见鹧鸪的叫声,看不见野兔和山羊箭一样射过清清涧峡和枞树林。只有婆婆崖上依然贴满了红纸和鸡毛,一张纸就有一个新生儿的小名,这古老的习俗还保留着,那些红纸在冷寒的风中火苗一样抖索。
踏着微现着白霜的山路,我感到一种凄清和落寞,这条路不知走过多少代人了,它依然仄狭不平。多少年来,只有游子循着这条脐带来寻自己的故里,如今父兄姊妹们却沿着它走向山外,仿佛雁阵横过黑土地,有些永远不再回返,有些成为村庄的另一种候鸟,飞得憔悴也飞得沉重。我不明白,我的父兄姊妹宁愿在异乡的屋檐下仰望明月或听淅沥雨声,尝那份背井离乡的酸苦,也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为什么?呵,我的木板桥,我的瓦屋和田园,我的久违了的乡音,为什么就让我感觉着一种化不开的苦涩,仿佛喝那山中的苦茶?微寒的晨光从河湾的山那边照射过来,照着我从前的篱笆和木楼,照着我孤单的身影。
只有父亲和那条老花狗迎我,那情形恍如一幅剪影和古旧的画图。火塘里燃着芭茅草,这气氛还是从前我童年时的样子,可父亲已经很老了,一把锄头在土地上写满了苦难,也几乎写完了生命的最后一个句点。父亲告诉我,我的堂兄因交不起各种收费才停建新房,原来的老屋已破败不堪,不能再住人了。借我的钱或许是无力还清了。我便苦笑,还不起就还不起吧。只是我不解,凭什么如今农民建房要收地下文物损坏费、矿物损失费?
火光映了父亲多皱的老脸,听他絮絮叨叨村里的人事,我的心情难免沉重。父亲说,八月中秋那天,春姨姑的媳妇因为多生了一胎,乡干部拆了房子,赶走了两头猪。小媳妇躲在山里三天三夜,最后刚出生的婴儿受风寒死了,媳妇儿便上了吊,几天后才被砍柴的发现。又说村东根生因交不起四十块钱的人头费,与干部发生争执,被绳子捆了,关在乡政府,至今也未放回。父亲在叹息:“这还像个世道么?”
我无言。但我深知,生活永远是美好的,阳光下的阴影终有消失的一日。我的父老乡亲世代劳作在田园,无怨无悔,忍辱负重,心地宽厚地面对世事,但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和对世道人心的认知,他们把困惑和希冀埋在心里,艰难地写着他们的人生。许多代人已老死在逼仄的田园,许多旱涝和灾祸都挺过去了,但如今兄弟姊妹却候鸟一样飞离热土,漂泊在陌生的异乡,他们是存着一份向往也怀着一份无奈的吧。
一只鸟在黑土地那边啼叫。水井上的绳索已经断裂了。远处有一两个年老的老农驾了牛无声地犁着很板结的泥土。山色苍茫,黄叶如蝶。一切都透着清冷。
一位作家在黄土路上踽踽独行,他手里的烟卷正冒出浓烟。他去看从前的老村长,村长的屋歪在山坡上,竹篱笆上爬满了荒草和藤萝。一只狗凶凶地对他叫唤,它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汉子是一个名人。名人敲村长的木门,村长花白的脑袋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让名人坐在灰糊糊的木凳上,开始上句不接下句地说起这村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唉,如今村子是真的冷清了,不想活人呢。年老的不能干活,年轻的不愿守这憋屈的日子,外去打工了。妹子媳妇们都在外面犯作风错误了,有的还得了病,偶尔回来一次也偷偷摸摸地像作贼。全村百十个劳力,去外的九十多人,田土都荒完了。外面的钱不好赚,这家里的地更不好种,就是种了,除去成本除去这个税那个费,到头来,一年的汗水养不活一张口了。所以都只好出去了,只好丢下这份田地和这穷家了。没出去的只有我们这些走不动的老废物和小伢崽了。出去打工的寄回几个钱,邮局还要想着法子,硬性配搭你不要买的东西……唉!”
……
村长老了,老村长的女儿和儿媳都在外面做很荒唐的妇人了。村长没法子,因为村长已经老了。村长年轻的时候很英雄,曾放过每亩十万斤大卫星,曾经造梯田造得十天十夜不睡。也曾让村里最年轻的媳妇姑娘和婆娘去轮流夜战水库工地,村长一人犯了她们所有人的作风错误,让一个军婚怀了双胞胎,让一个寡妇生了丫头。那时候村长权威,犯了作风也没人敢放一个屁,不过如今这个村已没有村长了,没有了村长,所有的田土就开始荒芜。作家叹了一口气,走出木门,他觉得这世界已很陌生了。
不能安守清贫的时候,人便学会流浪。村庄上空已不再有悠悠的雁阵,村庄就像一部古旧的农书塞在山缝里,只有岁月的风在无声地翻弄。
父兄们哪里去了?童年的伙伴哪里去了?姊妹们哪里去了?他们像被风吹散的树叶。有一个叫岩保的伙伴去了南方,他是一位光棍,据说从工地的脚手架上跌下来,断了一条腿;有一个叫梅香的少妇,也去了南方,嫖客在她身上发泄完性欲后用水果刀割断了她的咽喉;有一个叫峥嵘的汉子,在外挣了大钱,却因重婚关进了牢房;而青儿呢,几年了,再没了音讯,青儿在村里时是常常替人写家信的……他们都从这个村落和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他们原本很年轻。为什么要离开土地,为什么要离开故乡,田也是人种的么,是畏惧了一世的苦,还是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引诱?父兄姊妹雁阵一样横过黑土地。有人回来了又走了,有人造了屋讨了女人,可他们还是走了,宁愿只留一个名字在村里,而许多名字的主人,土地已把他们遗忘。
不知道这世代播种着汗水和泪水,收获了贫穷也收获了快乐的田园为什么要被人厌弃。田园,美丽且苍茫的田园呵,你到底怎么了?是你的泥土不再养人,还是你中秋的明月不再浑圆?是你的阡陌不美丽,抑或是你的山歌和炊烟不再温馨?为什么人没有了眷恋?为什么人要逃离你的庇护,宁愿去漂泊?
在寂静的月影里,我凝望着这无言的村庄,想起它落着大雪时的动人景象和春花灼灼的晴和,想起它的沧桑百劫和丰收平和,想起童年的嬉戏和无忧,想起许多的人和事。我仿佛明白了人或许是应该离开故土的,只要心中装着,哪怕在天涯,也会感觉着它的存在和召唤。我是和那些父兄姊妹一样充当着游子,可是这脚下的田园永远以无言的美丽与亲情召唤着远方的灵魂。
人,或者就应该是故乡的候鸟?
但是为什么?!
(摘自《父老乡亲哪里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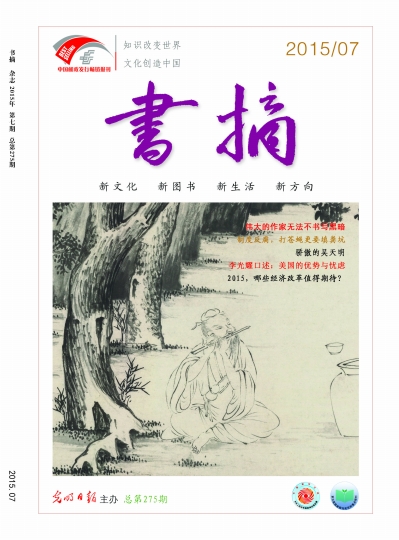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