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先生搬入念楼十多年了,与“念楼”有关的书出了好几种。其中《念楼学短》我尤其喜欢。所选古文皆百字以内,且独立成篇,以倡好文贵短的意思。每篇古文均配以“念楼读”及“念楼曰”,加起来亦不足三百字,却耐得咀嚼,经得看。还有一本《念楼集》,所收文章大半都是在念楼写的,我也喜欢看。
“念楼”乍一听恐怕有人不太明白来由。其实“念”就是“廿”,二十,钟先生住二十楼,由于“户户外貌咸同”,便在门口挂了块竹形直额,上刻“念楼钟寓”四字作为标志,并无其他什么特殊含意——固然钟先生对“念”字本意可能心有戚戚焉。
门口的这块直额其实是一塑胶仿铜件。原件挂在客厅墙上,为钟先生的友人浙江桐乡叶君精镌,堪称竹刻佳作,“念楼钟寓”几字则是钟先生集自周作人的手书。因担心损伤竹材,不敢硬钉,才另外请人仿制一件,固定在门外。
现在钟先生的书房系由客厅兼任。原先那间书房太小,于是钟先生与老伴朱纯合计,搬到客厅里了。反正来的客人多是谈书看书的,这样做正合适。客厅约三十平方米,算大的了。窗户朝南,书桌呈斜角置于窗下,光线很好。东西两面墙壁各置一排大书架,多为古籍或工具书。当然,《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李锐全集》等书也占有重要地位。朱纯大姐因此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老头挪书房》,饶见情趣。客厅中间则放了一张台球桌,不大,原先我以为是钟先生将其缩小尺寸请人定做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张标准尺寸的美式台球桌。钟先生不好动,读书写作之余唯独喜欢和老伴打打台球。可惜老伴去世多年了。
钟先生并不好收藏。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一辈子与书、与读书人打交道,多少总会留下几样或有意思,或可纪念的字画、摆设之类。还有些东西,则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情感有些关联,初看并不起眼,更谈不上贵重,说起来却有来历。譬如一九七六年在劳改队里给妻子制作的竹筒,一九六八年自制的欧洲式样细木工刨,还有他女儿从巴黎购回送给他的书册形木盒,以及友人从旧金山购赠的十八世纪北美移民用铜灯等。这些东西摆在书架上,不占地方不动声色,却悄然散发着一种温馨而亲切的日常生活气息。
钟先生说,本来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手艺很好的工匠。此言确实不虚。就拿他在牢里面制作的那个竹筒而言,上刻竹叶数片,并题上“斑竹一枝千滴泪”,堪称精美,更何况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用极其简陋的工具雕刻出来的。钟先生却笑言,因刻的是伟大领袖的诗句,才能公然为之。其实这句诗也有暗寓之意,它饱含了钟先生在牢改队里对妻子的深深思念。再说钟先生手工制作的两把细木工刨,也可圈可点。其时钟先生和妻子都在街道工厂做木模,并兼搞一点设计制图,可以温饱,所以还有点余暇和兴趣做几样喜欢的工具。这两把刨子做工、材质俱佳。一把刨身是血椆,底板用黄檀,前后手柄为梽木,木楔用花梨,另一把全部用名贵木材黄檀制作,材料居然来源于“破四旧”砸烂的古老家具,堪称“废物利用”的典范。
说到古老家具,钟先生至今仍有一件事情不无惋惜。故事发生的时间更早,即“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的他租住在北门余家塘一栋老楼里,房主是一位曾出任过民国时期最高法院院长的老先生。此公担心一房好家具迟早难保,有意将一张紫檀木雕花大床作价八元卖给钟先生。钟先生想反正睡觉也要张床,何况此床既好且大,睡个两三人还可余出一边堆书。可惜钟先生的父亲执意阻止,不愿“右派”儿子有半点张扬。结果此床被长沙民族乐器厂买下,且当即一顿敲拆,悉数散去做胡琴了。
钟先生委实在任何困厄的处境中仍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张力和乐观精神,并且在个性被极度压抑的时代仍能头脑清醒,坚持独立的自由思想。固然,他被报社打成“右派”也恰恰就因了“错就错在有思想”。即便在劳改队服刑期间,他也曾在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的帮助下(即以那位工人的名义借阅)通读了《二十四史》。通过读史,更加增强了钟先生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
在钟先生保存的个人物品中,时光印痕最深的应该是他父亲教他读宋词的手抄本。当时他父亲已七十岁了,钟先生却还只是读高小的年纪。钟先生说,小时候他们父子出去,人家把他们当祖孙辈看。我开玩笑说,看来晚年得子此子必定聪明,确有印证。钟先生却说不不,我哥哥比我聪明得多。还说自己儿时初学四则应用题“鸡兔同笼”,就蠢到了极点,居然去问父亲,谁会把两只脚的鸡往四只脚的兔子笼里赶,还不怕麻烦去数多少头多少脚?气得他的老父亲直翘胡子,大骂儿子“下愚不移”。
当然钟先生说自己蠢,不过自谦而已。他拿给我看的一卷文言笔记便是早在十五岁时候写的,题目叫做《蛛窗述闻》,且有弁言、有条例、有目录,很像一回事。其弁言俨称“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说他年少聪颖并不过分。钟先生自己现在还喜欢,并且推荐我看其中一篇《槐抱榆》,极短,读来果然有味。兹录于下:
平江女师校址故县署也中有大院落其角生一巨槐苍纹斑驳大可数抱其干中空而生一榆大亦抱馀二树之柯叶荫全一院树下有碑篆文四字云槐抱榆记下更有小字则模糊不辨矣
有时在钟先生家里聊天,他还特地要我替他拍一些保存多年的友人书信和题赠字画做资料。其中不少真实印证了数十年来钟先生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交往,更是颇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特择数件以记之。
钟先生自己觉得最为珍贵的手书,恐怕要算周作人在一九六三年亲笔写给他的回信了。钟先生曾将此信嵌入一镜框,挂在念楼书房的墙上。记得他对我说过,如果没有这封回信,谁会相信在那个蒙昧年代,一位被开除公职、砸了饭碗,以拖板车为生的三十出头的青年,竟然会与素昧平生,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过信呢?更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因打算重新出版周作人的著作,与其子周丰一取得了联系,某次,周丰一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发现了钟先生寄给周作人的那封信,遂将其影印寄给了钟先生。
极难想象,年轻的钟叔河当时能在信中如此写道:
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此信当时落款只有日期未写年份。据钟先生后来查阅周作人日记原件,确认此信写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因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上午得吉光二十五日信,钟叔河二十四日信。”
七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钟先生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十年。
钟先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周作人的喜爱。早在他八九岁的时候,看了兄姊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便喜欢上了《故乡的野菜》和《金鱼、鹦鹉、叭儿狗》的文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人归人,文归文”的观点,执意重印周作人的著作,更显示了他的胆魄和识见。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张中行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八岁。钟先生因此写了一篇情感深沉而真挚的纪念文章。文中写道: “张先生走了,走得像平时一样安详。先生年近期颐,已臻上寿,顺生应命,无疾而终,我辈本无庸过悲,但想到寥落晨星又弱一个,心中的失落感仍久久不能散去。”
钟先生与张中行两人堪称地道的君子之交,几乎从未涉及任何具体的世俗事端。张中行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最初两人相见的情形:“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我住河之北,相距弱水三千,只今年夏天他北来,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一面,招待他一顿晚饭。他著作等身,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就要‘超’身,可是我手头只有两种,其一是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掏自己腰包买的,其二是《书前书后》,是他北来过访时当面送的。”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张先生长钟先生二十二岁。钟先生认为,人之相与相知,并不在乎形迹。尤其是文字之交,鼎尝一脔,即已知味,更不必用作品相酬答。钟在后来的纪念文章中还写道:“他对我奖掖逾恒,我在他生前却从未公开写过他(先前对钱锺书先生也是这样),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爱重先生,亦爱重和先生的交谊,故深惧同于流俗贻先生羞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钟先生曾从梁任公集宋词长联中截取两句,单独集为一副对联。上句是辛稼轩的“更能消几番风雨”,下句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此联堪称绝妙,也暗合了钟先生当时的某种心情。后来钟先生请张中行题写,张先生欣然应诺,随即便将对联写好,在北京装裱后装盒寄给了钟先生。
在翻看和拍摄钟先生保存的这些个人字画书信中,他本人题写在一卷线装册页上的一首五言律诗令人颇生感慨。这首五言律诗是钟先生五十岁时写给他的患难之交朱正的:
同届知天命,相从三十年。
论交吾与汝,知味米和盐。
监房分饼宴,报社卖文钱。
却忆青春事,华发两萧然。
钟先生在内心里其实是个非常骄傲的人,能将其视为知己并且惺惺相惜的人恐怕寥寥。但朱正肯定是其中之一。他们两人的友情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历史。钟先生与朱正同年同月生,解放初期两人同时进入“新干班”学习,随后都到《新湖南报》社工作。一九五七年两人又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两人再度一起成为反革命分子。朱正被判刑三年,钟被判刑十年,且被关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此一系列的巧合堪称奇迹。在狱中朱正断言,“我坐三年是会坐满的,你坐十年肯定坐不满”。言下之意是不用十年时局会有巨变,果然言中。六年后“文革”结束,九年后钟先生平反出狱。而朱正当时的胆识可见一斑。
更有意味的是,两个人从年轻时候起,钟叔河偏爱周作人,朱正则偏爱鲁迅,且两人均成为了海内外研究周氏兄弟成就斐然、屈指可数的专家。
如今,距离钟先生写这首诗的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同年同月出生的两个人已八十出头了。
但钟先生对于生死的态度非常旷达而淡然。他特别喜欢杨绛女士介绍的兰德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难道不是最顺其自然的生命态度吗?
(摘自《众说钟叔河》,华夏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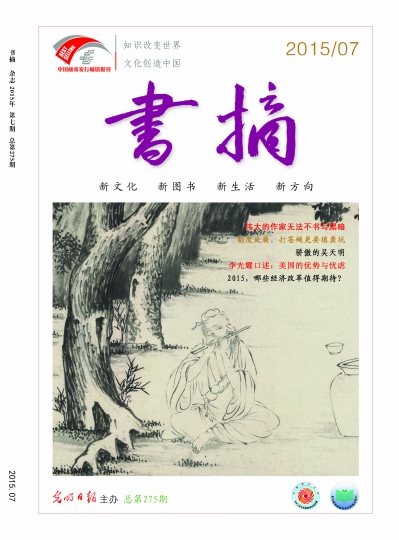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