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总在写信
200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拜访陈之藩。当我到达香港中文大学火车站时,陈先生早就从山上到山下接我,使我感念不已。多年后,我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文章《儒者的气象》,才有所悟:“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国,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约克镇研究所正在动工中。我到IBM面谈时,是在辛辛那提小镇。从火车上下来,还提个大箱子,来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车站来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抢过去为我提着。我那时还想,美国原来也是礼仪之邦啊,使我相当吃惊。”
我们一见如故,聊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共进晚餐时还谈兴甚浓。临别时,陈先生说,他在中文大学并不忙,希望我到香港就找他聊天。以后我每到香港,必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每次,我们都聊大半天,陈先生必请我吃晚餐。有一次,他说有一家上海菜馆极好,竟带我从中文大学坐火车到尖沙咀大快朵颐。
陈先生喜欢听我讲到各地采访人物的趣事,我则爱问他一些前辈的逸闻。我听得最多的是胡适和爱因斯坦的故事,不禁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
陈先生喜欢讲笑话。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所在的大学,敲门自我介绍:“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 “你爱说中国话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侠?”
陈之藩说:“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
王浩说:“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
两人争了半天,王浩突然说:“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
陈之藩是剑桥大学博士,对金庸到剑桥读博士,自有看法。在我看来,金庸有没有博士学位,一点也不影响我爱看他的小说。如同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不是真的,也一点不影响我佩服他的思想。
陈之藩一生,给我的印象是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我有幸珍藏几封陈先生的信,每次重读,如沐春风。
悲观而又爱国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十三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在胡适的朋友圈中,陈之藩也给金岳霖、沈从文写过信。他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改专业的决定,陈之藩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金岳霖问:“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
陈之藩说:“我悲观而又爱国。”
“什么叫悲观呢?”
“我不知道。”
“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
一席谈之后,陈之藩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学。后来陈之藩写了《哲学与困惑——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一文。
金岳霖写信的方式也给陈之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写信有好多种,中国式是从右到左竖着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着写,现在大陆也横着写。金岳霖是从左到右竖着写,他怕他手粘墨。”陈之藩笑着回忆,“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儿。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说这话时,陈之藩禁不住又鼓起掌来。
大概是在东厂胡同看了胡适的第二天,陈之藩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跑来跑去。沈从文就做了介绍。当时陈之藩的学校两千人,只有三四个女同学,没见过漂亮女人。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之藩想象之外,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一会儿就好了。”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主要工作是修马达,实在无聊。他在北洋大学的老院长李书田在台北的国立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组,便叫他过去工作。当时梁实秋在国立编译馆主持人文科学组,一看陈之藩写的文章就说:“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这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后来梁实秋成了馆长,说要提拔天才,把陈之藩的薪水加了一倍。陈之藩领到工资时并不知情,便去找会计:“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会计说:“你们梁馆长批的。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会计以为陈之藩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同乡。
胡适第二次回到台湾时,陈之藩去看他。胡适说:“你几时回来的?”陈之藩说:“我从哪儿回来?”胡适说:“美国。”陈之藩因为经济拮据,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去美国留学。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用作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这时陈之藩还没有钱买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借路费,便延迟了一年赴美,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出了书,拿到了去美国的路费。
1955年,陈之藩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科学硕士学位。陈之藩赴美,正是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在春风里》序)
陈之藩获得硕士学位后,应聘到曼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这时才有能力分期偿还胡适当年的借款,当他还清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胡适的风度和胸襟,陈之藩写得让人想流泪:“生民涂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躏人权的事,他看不得;贫穷,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却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他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这是他力竭声嘶地提倡科学,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里所想的科学与民主,翻成白话该是:假使没有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调子。而他所谓的科学,只是先要少出错,然后再谈立功。”
1962年3月11日,陈之藩给天上的胡适写信:“适之先生,天上好玩吗?希望您在那儿多演讲,多解释解释,让老天爷保佑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我们这群茫然的孤儿。大家虽然有些过错,甚至罪恶,但心眼儿都还挺好的。大家也决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学您一德,希望您能保佑我们。”半个世纪之后,陈之藩和胡适在天堂相会,相信不再寂寞了。
剑桥聊天录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以我对陈先生的了解,他在剑桥最爱做的事自然是聊天。重读《剑河倒影》,我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先生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摘自《读库·1406》,新星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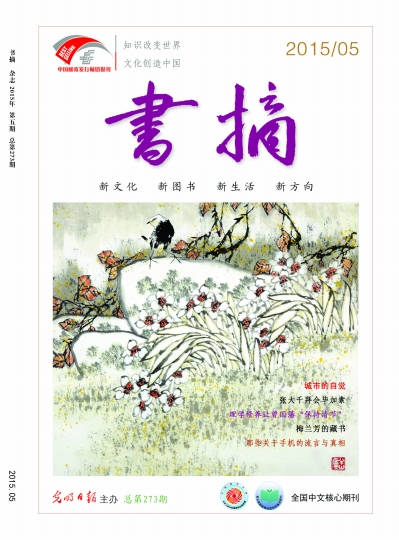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