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两次在长沙“念楼钟寓”拜访钟叔河先生。
第一次是2003年11月。因为有大哥卫建民的介绍,钟先生没有任何客套,平和地把我让到客厅的沙发上。宽大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台球案子,想来是老人平时编书、写书累了,便打上几杆,舒活筋骨吧。地板是锃亮的黑色大理石,墙上挂着沈从文、黄永玉的字。
紧靠沙发是一个躺椅,老人就靠在躺椅上,用极富韵味的湘音跟我聊起来。此前我已读过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深深折服于钟先生的思想和文采。书中收集的是他为《走向世界丛书》里每一部书写的叙论,他给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锺书先生“主动”给此书作序,称首次在《读书》杂志看见这些文章,“就感到惊喜”;又说,“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钟先生早年饱历苦难,一双眼睛却依然那样清澈、纯净。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钟先生腹笥之广和惊人的记忆力让我叹服。临走时钟先生引我到“念楼北屋”,指着满书架他的著作,问我要哪几种。我选了《念楼集》和《书前书后》。老人坐在书桌前签名,又找了一个信袋,把书装进去递给我。几天后我就把《念楼集》读完了,特别喜欢书中那些浇胸中块垒、“多言外意”的钟氏风格的文字。我给钟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回信,我从回信里真切感受到钟先生虚怀、求是、谨严不苟的风范。
八年后,即2011年3月,我第二次去长沙,住在岳麓山下的枫林宾馆。我有个愚见,人跟书一样,有的人似中外古今的名著名篇,滋味绵长,常读常新。在我眼里钟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于是下榻后来不及盥洗,就跟钟先生电话约好,公事结束后去念楼拜访。电话里钟先生的声音中气十足,语音清晰,全然不像年过八旬的老人。
那天是个周末,出租车在橘子洲大桥遇堵。接连两天都在下雨,现在雨停了,天还是灰暗阴沉。从车窗看出去,橘子洲、长沙城笼罩在蒙蒙云雾之中。下午5点钟才来到营盘东路38号那座高层住宅楼下。物业很好,楼道、电梯洁净如洗。上到二十层,出电梯左拐,迎面看见防盗门上铸铜的“念楼钟寓”。保姆小谢应着铃声跑过来开门,钟先生已站在门厅了。
与八年前相比,钟先生脸上多了几处老人斑。钟夫人已经去世,我感到念楼里不免有些孤清。客厅靠窗多了一张书桌,上面摆着正在校阅的书稿。那张台球案子依然摆在客厅中央。
落座后,钟先生顺手拿过一张校样给我看,是胡适手书的长卷。一边说:“这是前些年出过的一本书,现在要重印。”又递过一册已出版的《林屋山民送米卷子》,说:“原来印得不好。本来是长卷,印的时候分开了,这次重印就印成长卷。”
我俯身看胡适那个手书的长卷,见上面密密麻麻、但又是整整齐齐地用红笔标明校正的字、标点和各种符号。这是钟先生一贯的风格。
书桌上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牛皮纸信封。钟先生告诉我,这是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亲笔信,说着取出信来,指给我看那一笔不颤不抖、不歪不斜、娟秀清丽的小字。钟先生还念出声来,对一些内容做着注解。征得钟先生同意,我用相机把信正面拍下来,留作纪念。
钟先生念完信,重新折好装进信封。他似乎想起什么,站起来,一边走向客厅靠墙的书柜,一边说:“我要送给你和你大哥卫建民一套书。”书拿来了,是两套,放在我面前的小方桌上。一套装在硬纸盒子里,一套没装盒子,码得整整齐齐。原来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新版的《念楼学短》,五个分册依次为,《逝者如斯》《桃李不言》《月下》《之乎者也》《勿相忘》。书的体例和版式与前些年出版的《学其短》《念楼学短》一样。钟先生扭过身伏在靠窗的书桌上,给两套书分别签了名。
我因为过几天就要调往大同工作,便请钟先生赐教。钟先生随手拿过一张白纸,稍加思索,写道:“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又在一旁注明,“这是知堂最喜欢引用的一句古人言”。
钟先生吩咐小谢多蒸米饭,留我吃了晚饭。
我在返回枫林宾馆的车上端详着《念楼学短》,这套书真是漂亮。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每本书的厚度几乎完全一样。回到宾馆逐册查验,果然除第五分册“勿相忘”是二百一十一个页码外,其余四个分册全都是二百一十三个页码。全书共计五百三十篇。这是多么考究、清爽、益智的一套书啊!
(摘自《双椿集》,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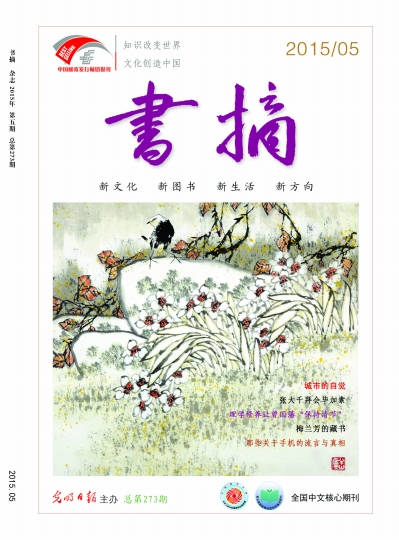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