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包含了大量战国至汉代的百科名词。当中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篇,乃“名物诠释之宗”(扬之水语)。对其价值,郭璞序认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过)于《尔雅》。”今人则指出,它是我国古代动植物分类认识的完整反映,将植物分为草(草本植物)、木(木本植物)两类,将动物分为虫(无脊椎动物)、鱼(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鸟、兽四类,已与现代生物分类学的认识基本一致。
韩愈诗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不管其意是自谦自嘲抑或讽刺不屑,历来热爱此道的人还是不少;我对《尔雅》的兴趣,也正在于草木鸟兽虫鱼而非该书其他内容,所以,后人的诸种《尔雅》诠释本,以宋代罗愿专门研究其所载动植物的《尔雅翼》(石云孙点校,黄山书社1991年10月一版)最合我意。
罗愿广征文献,又注重目验,《尔雅翼》在《尔雅》释名的基础上,进而探究源流,甄别名实,说明形状、特性、功用等,兼考论音义语用,纠正了前人不少谬误。《四库全书提要》称许其“考据精博,而体例严谨”。扬之水研究《诗经》也列为重要参考书,赞赏“它的引证,说详也可,说杂也可,总之每一则都可以作故事读”(《诗经别裁》前言)。
其中“释草”120种、“释木”60种,自然是我关注的重点内容。六月中旬得书即夜、在近来日夜不断的狂雷骇电大暴雨中,读了“卷施”、“卷耳”两则。
事缘近十年前,购得淦女士(冯沅君)的小说集《卷葹》,这个带着古典诗意的书名,颇勾起我的兴致。查到鲁迅曾把此书编入“乌合丛书”,写信给陶元庆请对方画封面,信上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也不知道。”连一贯喜爱草木虫鱼的鲁迅都不明所以,我当时就手头的有限资料查索一番,也未得确解。情形大致如下:
“葹”,见于《离骚》:“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葹一般解作苍耳,与菉(淡竹叶)一起泛指恶草。苍耳又名葈耳(王逸仿《楚辞》而作的《九思》,有“椒瑛兮湟污,葈耳兮充房”句,意同于屈原),乃一年生菊科植物,春夏开花,果实有毒、有刺,易附于人畜而传播(故又名“羊带来”),到处杂生——这些是它被视为恶草、喻指小人的原因。
《诗经·周南》有《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一般认为卷耳即葈耳,叶如鼠耳,丛生如盘。——卷耳的叶、苗、种子可以食用,是古代的野菜,《诗经》时代人们就采摘了,然则它并不全是《离骚》里的反面形象。
但让人疑惑的是,其一,据《辞海》,今天植物学上的卷耳并非葈耳,而是多年生石竹科植物,没有上面说的特性。其二,当时手头典籍中,找不到冯沅君那样的“卷葹”组词。其三,如何“拔心不死”,也不详明。
到今夏,前些时在明人王象晋《群芳谱》中读到《卷耳》一则,写得很有情味:“宿莽也,一名葈耳……性甚耐拔,其心不死。可以毒鱼……入书笥中,白鱼不能损书。”这里说的仍是古之卷耳(苍耳、葈耳、葹),由此知道“拔心不死”、“拔了心也不死”可有两解,一是拔去其心(芯)仍能活,二是“性甚耐拔,其心不死”,总之都指其生命力强。(故而非常易于生长,加上其果实的黏附性,乃成为难以防治的杂草。)
现在读《尔雅翼》,得到进一步了解,却也产生新的问题。
原来,“卷施”一词见于《尔雅》,冯沅君的书名是有出典的,只不过易为“卷葹”,更加古色古香。《尔雅》“释草”谓:“卷施草,拔心不死。”郭璞解作宿莽,说《离骚》中的“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就是卷施。王逸则指宿莽“遇冬不枯”,正与木兰的“去皮不死”合为君子象征。
指宿莽为卷施,除了郭璞,还有罗愿《尔雅翼》引《南越志》的佐证;但也有不同意见,潘富俊《楚辞植物图鉴》引历来纷纭众说后,认为宿莽应是莽草,李时珍《本草纲目》谓莽草“有毒,食之令人迷惘”。
《尔雅》“释草”还另辟“卷耳”条,罗愿的笺释,其性状等与前引“葹”(苍耳、葈耳)相同,也就是说,葹(卷耳、苍耳、葈耳)归葹,卷施(宿莽)归卷施,是两种植物;而王象晋《群芳谱》则视两者为一。
于是,葹与卷施,古称的卷耳与今称的卷耳,牵连所及还有宿莽等,组成了一片迷离草色,始终让我目乱。然而,时隔近十年的两次翻检诸书,总是一番纸上踏青之乐。我最喜欢的还是王象晋那条典故:不管是宿莽(卷施)还是葈耳(葹、卷耳、苍耳),不管其他正面价值与负面意义,这种草能防蠹鱼(白鱼)损书,就是读书人眼中的可爱植物了。
(摘自《闲花》,中华书局2014年10月版,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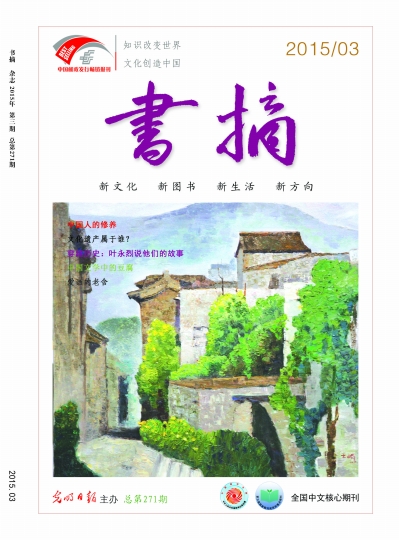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