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为书而作之书。作者以淳朴的心情、在寻常可遇的读物中,从辛亥革命那年起,作了一次年轮式的阅读,可谓匠心独运。书里书外的短文,史料丰富,时见精彩,即是书的“年轮”,也侧印出人的“年轮”。
1911年
《少年》杂志
十四岁的费孝通遇见自己的文章发表于《少年》杂志,“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思。
主编该刊的孙筑修先生,曾于科举废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童话编写中国儿童读物。在其陆续主编的百多种童话中,由他自己编写的计七十多种,在儿童文学于中国形成系统的初期有筚路蓝缕之功。《少年》杂志创刊时,其为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自创刊至终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润了多少中国少年的生命。
1948年夏,钱锺书、杨绛夫妇带着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锺书祖父做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一间厢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视的。大概钱家的孩子无人不读。
人称“文学圈外文章高手”的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文字生涯即开端于这本刊物。他早年文学兴趣很浓,读到初中时,一位亲戚为他订阅了《少年》杂志。费孝通从此成为该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都是从头读到尾,一篇不落,几期下来,这位少年已不满足于仅当读者。他要成为作者。
当时的少年,头脑里有许多从祖辈、父辈那里听来的、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费孝通在记忆中的故事里选出一个,写了出来,向该刊投稿,署名“费北”。
一个新年里,他收到了当年第一期《少年》杂志,照例细读,却不知已有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读到最后的“少年文艺”专栏,费孝通见自己投寄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文已成白纸黑字,遂“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费孝通晚年回忆那次经历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地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之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细察费孝通一生,不惟发表文章、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成其终身爱好,写作不辍,“开卷第一篇”的荣耀感更为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时期备下自信。
1924年
《汉书艺文志讲疏》
能跟在一位学养丰富的读者之后,待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
在1924年的出版物中,碰上的第一本就是《汉书艺文志讲疏》,是东吴大学的“东南大学丛书”的一种。尚未翻过开卷之页,就被该书流传过程中留驻于该页的印记吸引。书名及班固、颜师古名下,是一枚“徐氏”藏书章,阳文篆刻,古雅、工整。书眉上的批注更是耐看,毛笔书写,蝇头小楷,馆阁体中略带行草,疏密有致,功力内敛,每字皆小于书上的正文铅字。边看边感慨,先不说写书人了,过去读书的人都这么有学问,比起来真是让人气短。面对“徐氏”书法,即便仅仅是自认为读者,也有滥竽充数之嫌了。
这么漂亮的批注,不时现于书页之眉,跳荡闪烁。一时间,对我这等既无慧根、又少定力的人,吸引力大过了书的正文。细察全书,眉批有八十余处。一一读过,感觉这位读者不仅字好,学问也好。眉批间有注疏,有评点,有考索,有订正,有校雠……等于扩展了该书的内容。能跟在这样一位学养丰厚的读者之后,待这本书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为此,特把其藏书章附录于书影,留作纪念。作为该章主人的“徐氏”若健在,希望有机会当面一拜,若已作古,则盼其有后人,并能看见这几行字,以寄托我的敬、谢之意。
1947年
《罗曼·罗兰传》
“俄罗斯这个伟大心灵的光焰照亮了大地……是照亮我们青年时期的最纯洁光芒。”
威尔逊著、沈炼之译的这本《罗曼·罗兰传》,是巴金当年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第四十种,初版本1947年5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后记”说,该书是从原版书作者的专题研究论文中翻译出的。原作并非传记,作为传记来读,可以说得通的一个理由,就是书中有罗曼·罗兰看重的丰富资料。例如,在一些说法中,以为罗曼·罗兰写给托尔斯泰的信只有一封,事实上共有七封之多,首尾两封之间,跨越二十年之久。这七封信的写作时间、内容,作者多有叙述。
罗曼·罗兰既以托尔斯泰为精神导师,则这些资料对理解传主自是重要。他对托尔斯泰的尊敬和崇拜,真挚热烈,在二十年时光中越积越厚,越酿越醇,到托尔斯泰逝世后终至火山般喷发。在《托尔斯泰传》中,罗曼·罗兰把其逝世比喻为“刚熄灭的光芒”,说:“俄罗斯这个伟大心灵的光焰照亮了大地。这个心灵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曾经是照亮了我们青年时期的最纯洁光芒。在19世纪行将结束时阴霾重重的暮色中,它是颗安慰之星,它的闪光吸引着、抚慰着我们青年人的心灵……我终于认识到他的那些日子将永不会从我的思想中磨灭。”
尤为可贵的是,当罗曼·罗兰发现有人往托尔斯泰身上寄托“党派感情”时,他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样的概念不应成为衡量天才的尺度。他说:“托尔斯泰是否和我一派无关紧要!在呼吸他们的气息,啜饮他们的智慧时,我会关切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哪一派吗?”
1978年
《哥德巴赫猜想》
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角,产生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影响。
这个书名,本是一篇报告文学的题目。作者徐迟在这书“后记”中说,从1966年到1976年,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以《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他“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进入喷发状态。《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为时代转换的一个强烈信号。
徐迟为做好这篇文章,读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华罗庚的《数论导引》,还有《中国古代数学史》等书。做过这些功课,徐迟除了采访陈景润,还采访了吴文俊、杨乐、张广厚等知名数学家,带着诗人的激情,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角,产生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影响。
1978年4月,《哥德巴赫猜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时,“七七级”大学生刚刚入学报到,坐定课桌,开始如饥似渴的求知和猜想。
1980年
《围城》
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
这本小说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从1949年到1979年,国内似没有再印该书,也不怎么提它,倒是旅美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很高评价,引出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版界对《围城》再度关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该书,钱锺书在“重印前记”中表示感到意外。
新版《围城》的热卖,把钱先生又一次变成了热门作家。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随后,这位朋友的一位朋友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的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
1996年
《老照片》
中国的记史传统何其悠久?百姓能走上历史前台,进入史籍,难得一见。
新时期阅读史上,《老照片》(第一辑)为读者打开了一片新的阅读视野。该书的老照片中,有周恩来会见柯西金,潘光旦笑迎毛泽东,也有女知青在田头,小孩子演样板戏,政要、学者、男女老少,市井烟火,寻常人家,一同登台。
百姓喜欢,专家称道,真正雅俗共赏,半年内,这本小书重印三次。
中国的记史传统何其悠久?史书何其浩繁?百姓能走上历史前台,进入史籍,难得一见。
一种可以叫做“图像历史”的意识,似乎在普遍觉醒,越来越多的图片进入编辑视野,不仅新书热衷图片,许多老书也以图片为翻新手段,重新登场。大量的豪华本、珍藏本、插图本,多以图片为招徕。
一位藏书极多的朋友说:图文书大行其道,《老照片》有开风气之功。
真实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分得出官场和民生,分得出庙堂和江湖,却分不出正野。如果一定要分,民众是本,才有资格居于“正”位。《老照片》为还原历史认真做事,对本来就生活在同一天地的士农工商官一视同仁,把平民请回历史,真正是“以人为本”,合了民意,顺了民心,才有了民望。
《老照片》温情中有深度,至味无味罢了。其绵延至今,不仅赢得了读者衷心喜爱,而且让历史这部大书从书架上走下来,变成了活动的、开放的、延续的、每个人都在其中的无字大书。有心即可读,读之自有味。
(摘自《纸年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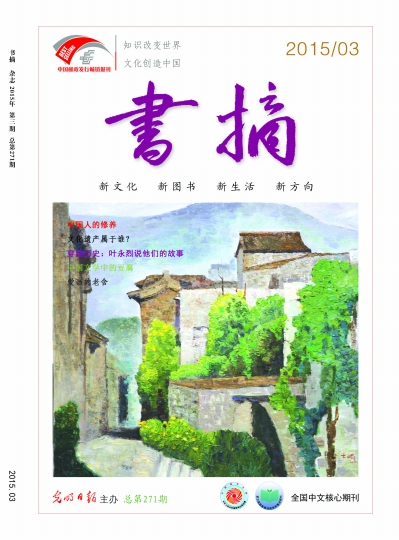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