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我平日读书,若有心得,都习惯批注在书里。而读书之外,时不时也有若干杂感,过去只随手写在零散的信笺或报章上,有些写成了文章,但有些无足轻重,也就付予尘封而已。
后来有一阵,也许是所感渐多,所思渐深,觉得写在书上纸上不易存留,心念一起,就决定集中写在笔记本上。
做学问不用怕艰深晦涩,不用怕别人看不懂;但搞创作,却应当好看,应当让人看懂。例如写诗还可以让人看不太懂,但写小说、拍电影总要让人看得懂吧!
据说爱因斯坦曾对卓别林说:“你真了不起,全世界都喜欢看你的表演。”卓别林则回答:“你更了不起,全世界都看不懂你的著作。”这就是做学问与搞创作的区别。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家族制度和观念在大陆逐渐消亡,我辈生长红旗下,多不知二代以上事。我自小就有一个印象:祖辈曾开过金铺。年前偶返开平看碉楼,问起父母此事,才知道原来是开过五金铺!不过,我姨丈家倒真是开过金铺,是不是我下意识地将姨丈家的事当作我家的光荣历史了?
其实人类所谓历史,其以讹传讹,亦大抵如是。
无论对于工作,或者对于生活,都需要有一种“敬”的精神。唯其“敬”,才能对工作勉力而为;唯其“敬”,才能对生活心怀感激。
日剧《午餐女王》里那个马卡罗尼餐厅的老板,三十年如一日地保守着他的牛肉酱风味,同时维持着价廉物美的午餐供应,就充分体现出对工作的“敬”;而女主角麦田夏美,每天抱着无比的期待、无比的热情,去享受一顿美味的廉价午餐,则又体现出对生活的“敬”。
那位老板甚至说过:就算明天日本就要沉没,也会跟平常一样卖蛋包饭,这跟马丁·路德所说的“即使明天世界就要毁灭,我也要种下我的小树”,在精神上是一样的啊。
在物质丰裕的年代,我们不必刻意地去“忆苦思甜”,但我们仍应当明白,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文化一旦定型,形成一种传统,就不容易摆脱定势,不容易自我革新了;故文化创新往往源自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借用,或者说,源自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
一种原生的象形文字,如不脱离本来的社会系统,那么就始终仍是象形文字(如古埃及象形文字、汉字),只有另一个族群借用了这种象形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才有可能形成一种表音文字(如朝鲜文、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汉喃),乃至拼音文字(如腓尼基字母)。
一种原发性的信仰,也只有在异文化的语境中,才有可能出现“升级”,形成一种超民族的宗教(如基督教)。文化输入的例子,如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并形成中国式的禅宗,更刺激了理学的出现;同时,梵文的传入,也促成了汉语四声的定型,由此又间接促进了格律诗——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旋律——的形成。也有文化输出的例子,中国的火药原是用来做爆竹烟花的,但到了西方人那里,却用来做弹药了;中国人习惯清茶一杯,不愿意在茶里放其他东西,而蒙古人却往里放酥油(酥油茶),东南亚人往里放排骨(肉骨茶),西洋人往里放奶和糖(奶茶),至少,奶茶是饮食史上的一大发明。
(摘自《反读书记》,花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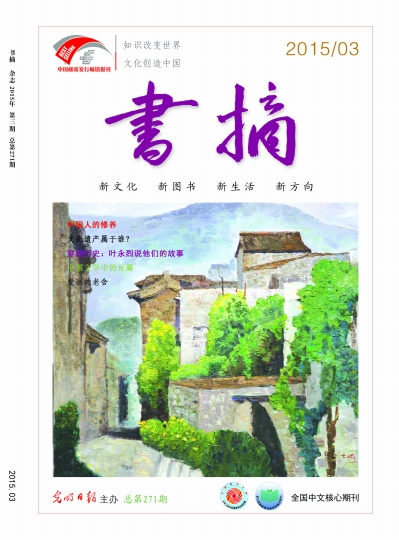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