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府州县官与士绅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来进行统治。在一个只是由为数不多的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士绅是中央政权不可不倚重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州县官根本不用指望在当地收取租税、维持治安。对朝廷来说,在安定时期,士绅的支持是重要的;而在动乱时期,更是决定性的。
在鸦片战争中,广东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乡勇。最高一级是“勇”,他们受到紧密的控制,是由正规军官指挥的。第二级是由士绅创办的。他们或是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或是同广州有密切的联系。第三级是真正的团练,他们通常得到了省级官员的批准,但其活动却独立于官僚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依次下降的顺序,从官方的到个人的,从中央的到地方的,从正规的到非正规的。
“勇”只不过是雇佣兵。1840年6月,广州府在商馆前面设立了一个招募新兵的机构。数以百计的壮士排队应募,试着举起100斤重的东西。如果成功了,他们就被编入广州协台的队伍中,附属于一支正规军,有每月六元饷银。
接下来是中间一级的。在这一级,士绅是省衙门的代理人。有些人,像杨永衍,就是“幕友”(私人秘书)。还有一些人,地位高一些,他们可以沟通省里与县里士绅间的关系,比如孔继动,就是南海县罗格围的一位著名学者。他1818年中举后,做过书院教谕,1833年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在北京的国史编修馆副修纂。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退休,但他同意做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非正式的军事顾问。由于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他同整个广州府的许多重要士绅有密切关系,他能够帮助林则徐安排地方防务。
这些中介人所接触的士绅,往往会为省里提供防卫经费。这些钱是否由家族或地方组织联合捐献,总的数额很难确定,但数目常常是可观的。南海县恩洲蔡文纲捐出的钱足以维持几个炮台的给养。东莞县著名士绅陈北垣捐献了七万多两银子以供地方海防之需。
1841年3月,当大批市民逃离受威胁的城市、涌向乡村地区时,地方官员要求更多的士绅协助维持秩序。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士绅在没有得到广州认可时就组织了团练。对于士绅们和不在位的官员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满足了现实的要求;面对当局的无能,他们认为那样的行动是必须的。例如,林则徐被解职以后很久,仍住在广州附近,自己出资训练了800名志愿者,即使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抢劫。顺德县的潘楷、番禺县的谢泽森、香山县的吴思树,都组织了这样的团练。
乡勇运动(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1841年5月保卫广州城的时期具体化了。按照夏燮的说法,所有用于防卫城市的乡勇均来自南海、番禺、香山或新安县。至少,从理论上讲,乡勇是以“户抽丁”(按户征集)的制度为基础的。每户三丁抽一。一百个应征者组成一个传统的甲,八甲组成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实际上,某一地区大总的规模可能只有另一地区大总的四分之一。这是因为,户抽丁的制度只是后来的一种附加物,而地方团练却已先存在了,而所有的志愿者必须在短短的10天之内集合起来并赶到广州。
在保卫城市中起作用的只有新安的乡勇。5月24日,他们配合八旗兵袭击了一些英国船只。其余的乡勇,尤其是那些来自番禺、南海县的乡勇,在5月22日归由官员们指挥,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却散乱为一群暴民,脱离了控制。他们的存在,从军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在于:清朝官员动员了乡村来反对英国侵略者,把数以万计的男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充满了愤怒之情。一旦签订休战协议,这些从未有机会真正投入战斗的乡勇们,会变得激动而愤怒,寻求着任何一种狂暴煽动。1841年5月25日,三元里地区的13名读书人在牛栏岗村(即后来英军被伏击的地方)开会,筹划在这一地区把团练组织起来。他们歃血盟誓,选出三名领袖,然后分头去各村动员。
三人中最著名并曾要求地方当局承认这次会议的是何玉成,他是举人,当地有名的文人。他前往南海县的东北部,负责那里以及与番禺县交界地区的团练活动。第二个是王绍光。他是候补县丞,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中的军功而获六品顶戴,负责组织番禺县六个客家村子。最后是梁廷栋,三元里以西恩洲的一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他把他领导的地区的12个“社学”联合成为一个防卫指挥系统。
他们的团练同官方文件中的“户抽丁”制度不同。它的组织不以“总”或“社”,而以“旗”为单位,通常写有“义民”和某一村庄的名字。这样的做法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支团练就代表着某一个人自己的村庄。乡勇们喜欢在本村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单位的旗帜下前进或后退。他们还有一面号令全体的黑旗,是从三元里的寺庙中拿来的,用以祛除邪魔。但是,这些乡勇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他们是地区的乡村单位的集合体。
如果每一支乡勇都代表着这种个别的忠义,那么,他们如何一起行动呢?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又如何组织起来呢?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士绅起了这种组织作用。只有在这种组织协调中,农村才能超越一个一个的乡村而在整个地区中组织起大规模的社会力量。通常,一名士绅会在一个乡镇周围组织起一支有号召力的团练。如林福祥,他在石井领导着“水勇”。他集合起他的人马后,就说服邻村的长老们把各自的武装都置于他的旗帜之下。当时,人们捐出许多铜锣,一旦某村出现紧急情况,只要鸣锣,别的村就会赶来支援。这样就从一个核心的团练组织扩展为组织较松散的“旗”。在这里,相比于农民的自发性,士绅的领导才是最基本的因素。
广东历史研究会的研究认为,当地大多数秘密会社参加了三元里事件。这同士绅的领导权是不矛盾的,也不改变运动的性质。研究还认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参加了这一事件。
当最初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城里时,一部分丝织工人放下织机,一齐前往三元里。这些工匠——人称“机房仔”,在广州的工作场所总是同寺院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团体在乾隆时代特别活跃,他们练习打拳、斗剑,还组成了一种吹打团参加民间节庆。
当然,还是要做一个结论:起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团练组织中的一类,依赖于士绅们得到官府准许的领导。
(摘自《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新星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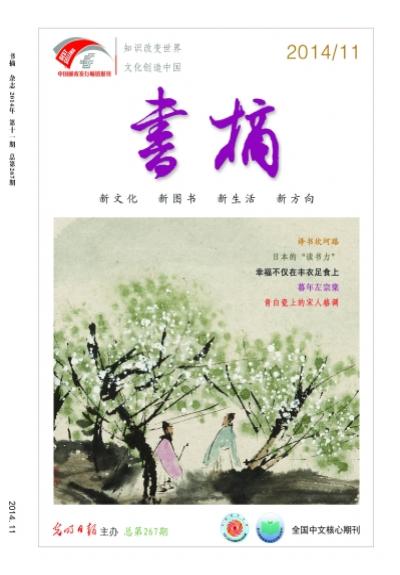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