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剑桥的高桌晚餐
一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M教授邀请我参加教员的高桌晚餐。
高桌,是餐厅专供教员使用的长条桌,它通常横摆在餐厅的主上方,那里的位置比学生餐桌的地面高出一两个台阶,师生虽然在同一个餐厅进餐,但师生的等级是由高桌来维持,因此,顾名思义,叫做High Table。从那里,教员可以俯视或监督低桌的学生,学生也有机会观察高桌上发生的事情,同时交头接耳,传播一些关于教授私生活的闲话和趣闻。不过,我在圣约翰学院做客的那天晚上,学生已放假回家,餐厅比以往都安静。剑桥高桌用餐的传统,和牛津、德莱姆这些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一样,在维持了几百年以后,至今依然如故。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爱恋,只要看看这些顽强保存下来的礼仪,就一目了然。我想,这不仅仅对我,恐怕对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会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对面坐的是一位圣约翰学院的资深院士,他自我介绍是语言学家。语言学教授懂得世界上二十多种语言,不过中文除外。晚餐期间,他特别喜欢和我讨论中文和汉字。比如,英国Cambridge(剑桥)这个名字译成中文怎么讲?为什么“康桥”的译法未能流传下来?语言学教授听得兴趣盎然。坐在右边的M教授插话道:你还记得Joseph Needham(李约瑟)吧?他抬眼看着语言学教授说。
当然,听说他的中文是自学成才的,非常了不起,语言学教授禁不住赞叹起来。
你猜,他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什么?
不知道,你听他讲过?
“香烟”。对一个初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字其实不好写。M教授用手比划着给语言学教授解释道,M教授在剑桥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他的中文底子很好。
我心中产生了好奇,问道:李约瑟在世的时候,你们认识他?
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下,笑了,M教授说:天下无人不识君啊。
语言学教授接着说:我们剑桥当年有一大批红色科学家,最著名的两个天才,一个就是生化学家李约瑟,另一个你恐怕没有听说过,隔行如隔山嘛,他是大物理学家贝尔纳(J.D. Bernal),外号叫“智者”。这两个人从上大学开始,就信奉上社会主义,到后来,一个支持毛泽东,另一个捍卫斯大林,至死不变,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剑桥有一批左翼科学家,真是意想不到,李约瑟和贝尔纳都是被认可的皇家学会的院士啊。
我忍不住又问道:除了这两个人外,剑桥还有哪些人属于左翼科学家?
语言学教授说:你听说过生化学家霍尔丹那个怪人吗?他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大数学家哈迪(有人译为“哈代”),生物学家郝格本和数学家莱威。让我想想,哈迪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到剑桥,他原先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我听说,他的宿舍里老是挂着列宁的巨幅画像。这人是一个疯狂的板球迷,在他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够得上伟人布莱德曼——唐纳德·布莱德曼被公认是最伟大的板球手——的档次,一个人是列宁,另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M教授好像猛地想起什么,他把手中的甜点勺轻轻搁在盘子上,转身对我说:上星期《卫报》披露了一条特大丑闻,听说《纽约时报》也转载了这个消息,你回去看看。报上公布了乔治·奥威尔1949年向英国情报部门递交的绝密黑名单,他的笔记本上另有一百三十五个名字,比我们先前知道的多了一百个人。
你是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吗?
正是这个家伙。从M教授说话的语气听得出,他对奥威尔很不以为然。
什么黑名单?谁的名字在上面?……我不觉愕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谁的名字?自然是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和地上共产党,还有他们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别林、萧伯纳、斯坦贝克;你信不信,就连纽约市长拉瓜迪亚也榜上有名,这人1947年就死了,和共产党有什么干系?还有我们剑桥人的名字,贝尔纳、布莱克特、普利斯特利,都统统列在上面。奥威尔这家伙是不是足够阴险?
听到这里,我来了研究兴趣:奥威尔是一个作家,他为什么向谍报部门递黑名单?文学和政治之间到底有些什么瓜葛?我心想,回去把这个名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
李约瑟和他的左翼朋友
李约瑟与鲁桂珍和李大斐之间的故事,在学术界流传很广,对外人来说,这三个人的亲密友情始终是一个谜,我也很好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李约瑟的妻子桃乐希·李约瑟,中文名叫李大斐。她很不简单,不但读了科学博士,生前也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夫妻双双都被选为皇家学会院士的情况,极为罕见。鲁桂珍是他的著名情人和第二任妻子。
李约瑟活得很潇洒,其中一个表现,是他爱女人——这辈子他爱过很多女人,而且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和李大斐实行的是开放婚姻。所谓“开放婚姻”的意思是,结婚后,夫妻双方不受限制,两人都享有婚外情的自由——有人把这种“开放婚姻”和东方的妻妾制混为一谈,其实很不一样——让人实在想不通的倒是,像李约瑟这样一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在婚姻上竟如此离经叛道。
李约瑟的叛道,并不特别稀奇,因为当时英国的风气大异于今日。例如李约瑟的朋友、剑桥物理学家贝尔纳,1922年和他的妻子艾琳·斯普拉格结婚时,双方也事先讲好,要实行开放婚姻。他们说到做到:斯普拉格生的孩子,贝尔纳都一律认作是自己的孩子,贝尔纳自己也情人无数。年轻的时候,贝尔纳居无定所,他在艾琳那里或一个情人家里住一段时间,隔些日子又跑到别的女人那里去住。
表面看来,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是“一战”后的一时风气,但其中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一代欧洲的年轻人在政治和生活方式上,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这里既包括反抗传统、崇尚自由和社会主义,又包括公开裸泳、自由恋爱、实行开放婚姻。像李约瑟和贝尔纳的这种开放婚姻,当时在激进的艺术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中蔚然成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人不能被资产阶级的家庭伦理和性别财产观所束缚。法国思想家萨特和波伏娃的开放婚姻广为人知,但从时间上看,他们比起李约瑟和李大斐的实验前后不出十年。
贝尔纳年少气盛,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说起话来更是滔滔不绝。他是一个富有思想魅力的男人,经常吸引一些有理想的女性在他的周围,而且,这些女性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左翼,“智者”这个绰号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位叫起来的,后来响遍剑桥。有一天,贝尔纳的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来了两名助手,都是年轻女性。她们好奇地向贝尔纳的博士生霍奇金——此人在贝尔纳指导下做研究,建树多多,196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打听,贝尔纳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吗?霍奇金也是一位年轻女性,她微笑着回答说,你们明天随便找个话题考考他吧。这两个人依然将信将疑。第二天上午,贝尔纳果然出现在实验室中,她们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话题拿来问他:贝尔纳博士,您对墨西哥的建筑有研究吗?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贝尔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说:先告诉我,你们想听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前的建筑,还是那以后的建筑?接下来,他给她们上了一课墨西哥建筑史,她们自然也是听得心服口服。
对这个人不佩服不行。英国皇家建筑研究会邀请贝尔纳去演讲的时候,他在演讲中不但大谈欧洲城市规划的历史,而且还论及现代数学拓扑学的起源,让建筑学界的专家们颇有些自愧不如。贝尔纳说,拓扑学的数学问题,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城市规划,它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一个城市共有七座桥,
你如何走完所有的桥,
而不重复其中的一座?
这个有趣的数学命题,是被欧洲的一位数学家于1736年在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提出的。
我早就留心到,剑桥左翼科学家在知识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们有点像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这三个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但他们各自的文学艺术修养极其深厚,绝不是浅尝辄止或者随意涉猎。这从他们的社会交往中也可见一斑:这几位科学家与欧洲前卫诗人和画家的往来频繁,有些艺术家成为他们相当亲密的朋友。
有一天,毕加索来贝尔纳家做客,几轮葡萄酒喝过,毕加索兴致大发,拿起一支油画棒,在主人客厅的墙壁上运笔如飞,顷刻间完成一幅“壁画”。这幅画至今还在,几年前被英国的一家医疗慈善机构所收藏,成交25万英镑。
我猜想,沃丁顿(生物学家,剑桥左翼科学家圈子的核心人物,李约瑟、贝尔纳的朋友)当时也应该在场,亲眼看到毕加索的现场表演,尽管我无法证实这一点。我的依据是,沃丁顿既然是贝尔纳的好友,而且对毕加索和前卫艺术家的活动了如指掌,那种场合怎么能缺少他呢?况且毕加索去英国访问,目的是为了参加贝尔纳组织的世界和平运动大会,沃丁顿恰恰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的推测不是空穴来风,有一件事足以做证明:我在艺术史图书馆查资料,在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书名叫《表象之后》,把书抽出来一看,作者的名字让我的眼前一亮——沃丁顿!这书原来是他晚年的一本艺术史著作。在分工如此细密的现代世界,一个科学家竟然撰写了一部艺术史专著,这可以说闻所未闻。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艺术是沃丁顿的业余爱好,写这样一本书,不过是过把瘾。但看完书之后,我马上纠正了自己的偏见。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作,不但立论平稳,材料扎实,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作支持,而且洞见多出,大有和艺术史专家一分高下的架势。
不难想象,沃丁顿对欧洲现代艺术的观察和研究,一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至少从他当剑桥大学本科生的时代已经开始,否则无法解释这个科学家为什么对巴黎的画家和诗人——尤其是他们的底细——如此知根知底,好像他自己就生活其间。
我一位朋友是经济史学家,很多年前我和她在一个研究所共事一年,后来成为朋友,无所不谈。朱蒂,是我这个朋友的名字。她研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很多年,对哈耶克理论的来龙去脉,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是这方面公认的专家。
朱蒂回纽约探亲,我陪她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看《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特展,中午在咖啡厅休息吃饭时,我忽然想起沃丁顿,忍不住向朱蒂介绍起这位英国科学家对欧洲前卫艺术的研究,并且特别强调,是沃丁顿帮我解开了立体主义之谜。没料到,朱蒂眉毛一扬,反问一句:
哪一个沃丁顿?
我一愣,她也知道一个叫沃丁顿的人吗?我把英文字母给她拼读出来,然后又补充一句,朋友们称他“沃德”。
朱蒂听完摆一摆手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大名鼎鼎的沃丁顿,他是哈耶克的敌人。
我将信将疑,难道这个沃丁顿是孙悟空,竟也跑到经济学的领域大闹天宫?
不会吧?我们俩说的是同一个沃丁顿吗?我迟疑地问。
嘿,不就是那个剑桥帮吗?她笑着说,眉毛俏皮地往上一挑。
贝尔纳他们?我试探道。
对。
还有李约瑟?
当然。
原来朱蒂对剑桥科学家的事迹一点也不陌生,她的博学再次让我刮目相看。临分手时,她嘱咐我,别忘了回头再看一遍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那本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里,哈耶克指名道姓地骂过沃丁顿。
真有那么巧的事?我受到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回到家后立刻把《通往奴役之路》找出来读了一遍。果然,哈耶克点名批评了以沃丁顿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科学家,并且把矛头直接对准沃丁顿早年写的一本书,叫做《科学的态度》。
哈耶克为什么会把英国左翼科学家当作敌人?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里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因为,那些科学家主张“计划科学”——“计划”这两个字,是哈耶克不能容忍的东西,并由此认定这些人是“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分子”,还说以沃丁顿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科学家“敌视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所代表的一切”。好大的帽子!沃丁顿,敌视现代西方文明?这个说法让我吃惊不小。
一个是经济学家,一个是生化学家,隔行如隔山,怎会成为冤家对头?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哈耶克是不是误解了剑桥科学家们的意思?
不过,思前想后,我对哈耶克的境遇开始产生同情,因为他的思想和学说,在“二战”前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并不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孤掌难鸣,处境艰难。设身处地想,我若是哈耶克,我多半也会生出这样的烦恼: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最具才华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一律左倾?为什么最出色的诗人、作家、导演、艺术家和知识女性几乎都向左转,即使不加入共产党,也纷纷变成社会主义的信徒?
乔治·奥威尔的黑名单
剑桥大学高桌用餐会上,M教授第一次提起奥威尔的黑名单,从剑桥返回纽约后,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
有的时候,作家的命运很诡异。奥威尔,他的《动物庄园》写成后,出版过程极其曲折,一度到处碰壁,书稿在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旅行,又被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先后退还。想当初,他的报告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由出版家维克多·郭兰兹一手策划出版的,郭兰兹是最早鼓励奥威尔走上写作道路的人,但是就连这位朋友也拒绝出版《动物庄园》,理由是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写得过于粗糙,文学上不成功。
公平地讲,郭兰兹是伦敦著名的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发起人,政治立场和亲苏态度肯定多少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他看不上《动物庄园》或许和这些背景有关——顺便说一句,他的名字后来也被奥威尔写入黑名单。但是在1944年,让奥威尔最为苦恼的,是他分别接到艾略特和燕卜荪写给他的信,这两个人一点不留情面,言辞直白,指出《动物庄园》有许多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地方,认为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艾略特和郭兰兹不同,他是有名的右翼保守派,燕卜荪也不是左翼作家,这两个人对《动物庄园》如此否定,对奥威尔来说自然是雪上加霜。
但接下来,事情变得迷离扑朔,甚至有些神秘兮兮。既然奥威尔的文学同行一致认为《动物庄园》写得不成功,出版社也不愿意接手,那么到后来这部书稿如何转眼交成了铅字?何况,书稿变成铅字远不是故事的结束,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动画片,几年之内风靡世界,与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并驾齐驱,成为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文学作品。直到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动物庄园》推崇为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将其划入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
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平时爱读侦探小说,喜欢设计精巧的奇诡故事和情节,可当我深入研究奥威尔的材料,特别是近年陆续曝光的有关档案,我受到的心理冲击已经不能用惊讶来形容,原来其中的奇诡和奥妙不仅超越了侦探小说,而且让人联想起近来十分流行的阴谋论。
故事说起来很长:种种档案材料揭示,《动物庄园》有幕后推手——正在这部书稿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英国谍报部门IRD忽然对它发生兴趣,并及时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IRD与军情六处有直接联系,他们动用的是国家资源,自然无往不利。《动物庄园》这本书不仅顺利出版,并且和《一九八四》一道,被译成了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中文等几十种语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普及。于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了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
奥威尔的故事其实还没有完。
冷战结束以后,一些罕为人知的内幕陆续曝光,在1996年,英国谍报部门IRD的部分档案开始解密。解密后的文件刚被送到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英国《卫报》的一名记者就马上跑去审阅。记者在编号为FO1110/189的活页夹里,发现了一份奥威尔在1949年向IRD秘密递交的黑名单,上面罗列了欧美两国进步人士的名字,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共产党的同路人,其中的三十五人的名字,最先被媒体披露出来——这批名单是奥威尔在医院养病时交给他的女友西莉亚·克宛的。克宛是IRD的谍报人员,奥威尔一直在苦苦追求这位美女,尽管他的追求不顺利,连求婚也被拒,但是他依然迷恋这个女人。当克宛告诉奥威尔,IRD需要搜集情报来对付斯大林和苏共的时候,他欣然同意合作,并从此开始了他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的双重生涯。
奥威尔与英国谍报部门合作的内幕一经曝光,惊动了欧美知识界和他的众多“粉丝”,一时间舆论哗然,奥威尔凭借谴责极权主义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忽然之间变得岌岌可危。七年之后,又有记者发掘新的证据,奥威尔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笔记本,这个本子长19.8厘米,宽16.5厘米,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奥威尔在这个笔记本里,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从A到Z,共一百三十五个人。每个姓名旁边都写有批注,表明这个人是CP(共产党),那个人是FT(共产党同路人),这个人是尤太人(我是有意不写“犹”,因为这个字,多半是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教士引入的译名,并且借此把欧洲的种族歧视和排尤主义植入了汉语。这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望文生义,误以为“犹太”是中国人发明的译名。其实,以元代文献记载来说,涉及到北宋时期最早来开封的尤太人,古人是把希伯来语的称谓音译为汉字“竹忽”或“朱乎得”,绝不是“犹太”),那个人是爱尔兰人,等等。真相大白,原来这个笔记本才是早先被披露的黑名单的真正来源。
历史之路竟是如此幽深曲折。
(摘自《六个字母的解法》,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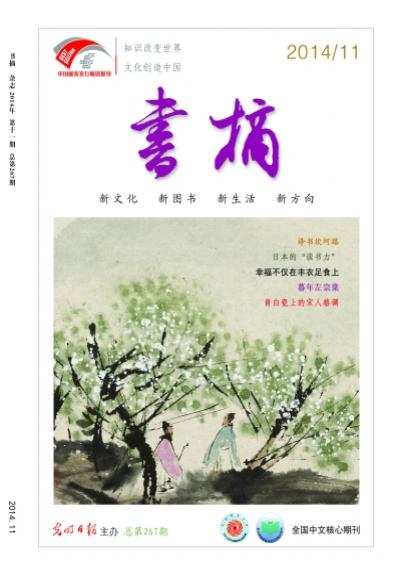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