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命运让死亡千差万别,却又用巨大的连成一体的沉默覆盖了这种差别。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每一个死者,哪怕只是眼神、手势或者气味。在人世萧条面前,请为他们留下遗言。
跳河的老人
一天,有个老人来到店里,买了两块饼干吃。关不紧的牙床,往外掉渣,一只手在下巴下边接着。他忘了把接到的渣送回嘴里,有几粒黏在了疏松的胡子上。他说,这一块钱还是小外孙给的。
他说上个月住在王家河坝女儿那里,这个月到期了,要下鸭河口儿子那里住。没人接他,女儿也没给车票钱。在女儿家里,饭他是在桌上吃的,虽说没有零花钱,也没添衣服。说好一边一年添一套衣服,可是儿子那边没添,女婿就不想添了。他的贴身裤衩、汗衫都穿烂了,不能洗,一洗就崩了。他戴的火车头帽子、穿的袄子,是冬天就穿着的。没有衣服是其次,他最难过的是到了儿子家里,不能上桌吃饭,要到灶门口吃。说是:老年人喜欢清静,专门给你端一碗菜,就在灶屋吃。可是那碗菜是昨天的剩菜占多数,饭也是剩饭。他简直恨儿媳妇,每回把饭菜做那么多,又不要他吃,像是存心剩下来叫他吃下一顿。
他说:儿子养了一条狗,在灶屋门口吃饭,也是有饭有菜。灶屋里还孵了一群小鸡,每天拿新饭喂。他觉得自己跟狗和鸡一样。他养了儿子几十年,老婆子死得早,他当爹又当妈,还养他上了初中。儿子养他不如养狗养鸡。
他说着眼泪滚滚,饼干都打湿了,没咬的半边耷下去了,好像被谁折叠。我想到达利画中虫蚀的钟表。他说他走不动了,才吃两块饼干,他怕是走不到儿子家了,他也不想走了,往路上一倒还安静些。路上那么多过的车,轰轰隆隆的,他耳朵已经要聋了。聋了也好,省得听儿媳妇假仁假义的话,听到他就难受。
岳母给了他一碗水。她说,本来想留他多歇一会,吃点饭,可又怕他真的走不到了。说起他儿子,也是开药店的,岳母认识。
老人走了以后,不久有人上来,说在鸭河口龙潭有人跳了河,是一个老汉。一问,就是他了。
外婆嘴里的橘子
我在想,要是妻子的外婆和跳河的老人遇到了,他们会说些啥子。外婆那不久前去的世。
外婆的房子我们去过一次。
门口一个鸡笼,鸡笼上一个大鸡窝。我和妻子的弟弟进屋,鸡窝里突然爆发出“咯咯”一阵狂叫,紧跟着升上空中,掀起风暴,母鸡像一架大飞机从极高处猛扑下来,夺门而出。
对面暗角里透出了外婆的床。似乎是肃穆的黑纱,其实是永远没有洗过的帐子的味,床沿有一个小口,小口透露出的乱被子凝结成一团,里子翻着,一眼之下心里油光光地硬、潮、冷。
一处地上打出个小坑,坑口有一小束烧了半截的桠枝。第一眼看了不明白,往旁边瞅,躺着一口半边眼的锅,心里才冒出“灶”的意思,吃了一惊。太微小,不像是真的。想到蚂蚁的窝。弟弟问:“外婆你弄得熟饭啦?”外婆没听懂,“哦”了一声,我又问,“你弄不弄得熟饭?”外婆絮叨:
“多于弄不成……火,又难得吹。半天吹不燃,眼睛瞅酸了,看不到了。渣渣儿都是找个人拣。有时候,我指望煮得熟哇,一烘就完了。饭煮成半生不熟的,又要去拣渣渣儿,又难得摸,半天拣一小把把儿。哦,引火的草还叫老鼠子拖去了……”声音也像一把渣渣儿。
弟弟喉咙就哽了,说:“外婆,你二回做饭,小心点儿啊,到处挂的是的……”我们都仰头,看屋梁上挂的那些影幢幢的干天星米、四季豆藤子,像要把房子堵实了。我也给外婆吩咐了一道。外婆“嗯”了一声,又说:“原先有个高炉子,我发不燃火,又没得煤炭了……”
我把火腿肠拿出来,外婆开了箱子搁进去,她喜欢吃火腿肠。箱子是老式的,放在鸡窝旁边一个土台上。箱顶上压了一张硬板纸,板纸上头的灰,箱盖一掀就层层落下。箱子还沾着一小坨鸡屎。
箱子底里,好像还有上年送的两封点心。我说外婆有东西你就吃啊,莫留,留久了硬了。也莫给孙子孙女,他们倒该给你呢。外婆嗯了一声。
外婆的最后几个月,搬到了幺舅家的一间屋里,因为外婆原来十年借住的一个外孙的房子,当时外孙在坐牢,现在回来了,收回了。不久外婆就病倒了床,说是不行了。她双腿水肿,半截都烂了,床单和身体是糊在一起的,说到这里,岳母就哭起来了,说“不忍心说得”,毕竟是亲生的娘。屋里非常冷,顶小一个炉子,幺舅娘成天蹲一个大猪食罐,一点火气都盖完了。那个猪食罐外婆的力气又挪不开。岳母为她擦洗身子,幺舅就对岳母很冷淡,出来进去横鼻子竖眼,后来两边果然吵了一大架。拖了一个多月,偏偏到外婆死的那两天,岳母因为店里没人照看,回来了两天,忽然接到信,外婆不行了。
岳母一口饭没吃完赶紧下去,外婆已经死了。岳母奇怪,外婆前两天精神还好,还和岳母说话,她好像终于明白过来了,说岳母对她最好,又说她死了,“不放过他们两口子”。幺舅说外婆是晚上死的。那天晚上,幺舅破天荒地要守夜。她们都睡了,第二天起来外婆就过世了。岳母发现外婆的嘴合不拢,里面塞了很多橘子。岳母再三问幺舅橘子哪里来的,幺舅承认他喂外婆吃过橘子。岳母回来说,“他肯定嫌她拖得太久了,总是怕拖到他大女儿过喜会,硬给她塞橘子,把她逼死了呢”。
外婆一天丧鼓都没打就埋了。外婆过世以后,幺舅接连遭了两次灾星:一是他得了伤寒,倒床一个多月;二是有一晚上,他在外婆原来住的房子里睡觉,加了火门窗关得死死的,结果煤气中毒了,口吐白沫,弄到卫生院好容易救转来。这两件事情发生以后,幺舅到外婆门前去了一趟,烧纸,恳求外婆保佑。
幺舅终究没免过。天知道他四十多岁的人,非要跑起摩的来,说闲在家里没事,在路上还能挣钱。挣了一个月钱,他在白沙河路口出了车祸。两辆大车一上一下,他在拐弯的时候超车,抵到了两辆车中间,夹得极死。
藤椅里的男人
四合院中间,一个人靠在藤椅里,阳光洒在他身上。医生站在他的面前,在他的小腿上开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他没有任何反应。血已经凝固了。
这是上午送来的喝毒药的农民,和女人吵架想不开了。送迟了,瞳孔散光,脉搏也没有了。可是医生把他弄到医院院子里,试一下。
医生用一台洗胃机,就是一台小手动机器连着一根长管子,把管子插进他喉咙里直到胃里,摇把一转,他的喉咙就剧烈抖动,看起来像要活过来一样,管子里面胃里黏糊的东西呼呼往外抽,进到一个容器里面。管子一停,他也就不动了。
医生看看他,又开始动作,他又剧烈抖动,开始还当他万一会活转来,这时已经觉得没有可能了,就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已经是死人了,不是人了,还坐在那里,和我那么近。虽然是大太阳,还是有种阴冷的感觉。医生还在抽,最后总算停下来,说肠子里的东西都抽出来了,不行了。
医生是在做实验,他是卫校西医毕业的,西医和中医在这事上是不一样的。医生又用针扎他的脚底,看他神经有没有反应,那针相当粗。我觉得他是在扎一件东西,可以毫无顾忌,比如那个三角形小口,可以随便在身上开,皮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叫我看的心里直寒。
人家说小孩子不能看死人,以至于我很久才淡忘。
豆腐客
豆腐客一般大清早下来,骑加重自行车,后架上搁一杆秤,秤下面一个小木箱,里头就是整整齐齐一大方豆腐。下车站稳了,四川腔:“要不要?”不要,依旧上车,一溜走了,不耽搁。
岳母店里是常买豆腐的,拿进来,还冒热气,从白沙河到这儿,十八里路,他身动得早,也骑得快!从不多坐,不多话,下小雨也来,披着厚雨衣,豆腐箱蒙着塑料布,照样是那么一声,“要吧?”那一声里,也许含有潮气;揭开包裹,豆腐却依旧温暖。下雪也来,豆腐比人裹得还严实。往下河还要跑十几里;中午大太阳,他推车上来,可没下来时那般轻捷;幸好卖完了。有时还剩下,看他推车的步,就更显出滞重,到店门前停下,默坐一会儿,年轻、严肃的神情,最多喝口水,抹嘴又走了。
剩的豆腐,发酸了,能卖也不卖了,回去要自己吃。
暑假回家,豆腐客换成骑摩托车了,不由想到他发达了。但不是那样推着车在路上招呼,是疾速而来,减速,稳稳地停到门上,人坐下,装上一根烟,看来打算好好歇气;慢悠悠的问:“要不要嘛?”岳母的反应也慢了许多,揭布看看,犹犹豫豫,“好像不多于好嘛”。
小伙子伸了一下腿,吐一口烟。“老板娘,你想要多好的豆腐嘛!”就是这一声,我忽然想到,不是那个小伙子了——口音是本地。
那豆腐也不好,煎时一翻就碎。岳母叹息说:“可惜那个四川小伙子死了。”
我吃一惊,问他怎么死了?岳母说淹死了。
我又一次非常疑惑,好好一个人,半年后就不在了。晚上寂静里,妻子忽然告诉我,他是叫人害死的,就是今天卖豆腐的那小伙子。
“听说他欠了那四川小伙子好多账,不想还,又霸他的豆腐坊……那天是他邀四川小伙子去逮鱼,到一个十多里没人烟的地方。他回来说,有一个地方,要从坡上爬过去,底下是大潭,四川小伙没抓稳掉下潭了。哪有那么凑巧?四川人一死,豆腐坊就转手到他手里了……”
我问公安上没查?四川那边没人来找?妻子说:“找啥子,总是塞得有钱,又没证据……豆腐客在四川还有媳妇娃子,媳妇过来收账,又是请他代收的。他原来没有职业,是赌棍。现在也一样,一早来,一早不来,往那一塌,豆腐也不卖了!”
在黑暗里,我的眼前,久久是今天那小伙子的面孔。眼睑臃肿,有一丝放纵的皱纹,奇怪的笑容,捻烟的发黄的手指,神经质的颤动。而豆腐客年轻严肃的面容,却逐渐模糊、消逝了。
也许是和我从未见过面的,那妇女和孩子的面容,融在一起。
(摘自《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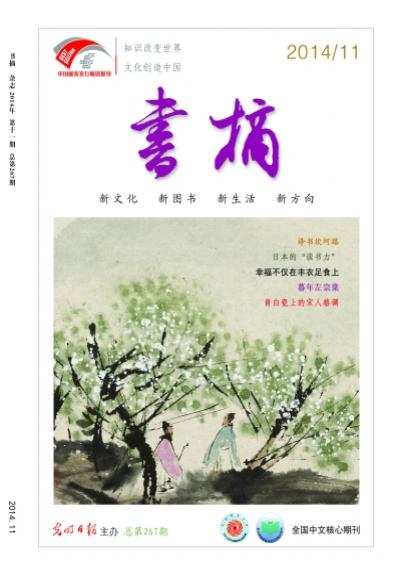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