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一个老人过世,我们就说一座图书馆烧毁了。”
——V.S.奈保尔《非洲的假面具》
我关于母亲的回忆,都很具体,很普通,也很琐碎,充满了各种细节,为我所感知——是那种无法脱离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知;回忆起来,却又微不足道,往往连件事儿都算不上。是以总有一种虚幻之感,稍纵即逝。
对我来说,母亲就是过去的一段生活;讲得夸张一点,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些生活习惯,或一份生活态度。然而这却是很难诉诸文字来表达的。
母亲是个普通的人。不像有的人生前有所建树,或有所创作,他们已经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在自己身后至少暂时保存下来;母亲去世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所感到痛惜者正在于此:一个普通人的死,真的就是结束。
当然也可以说:普通人死一次,而创造者死后有可能再死一次——作品之死,乃至名声之死。所谓“创造物”,有可能与一个人留下的遗物一样,自己不扔,死后别人还得扔。历史上大概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摆脱这一命运,不过也还不能就此断言,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许有些我们现在以为不死的人会陆续死掉。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人,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作品与名声的存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普通人反而没有这种危险。
母亲所曾经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那种有意味,有品质,又是平平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久久记忆,时时回想的,也是曾经如此生活着的母亲。我惋惜哀痛这种生活与母亲已经一并不复存在。
母亲的“地标”
母亲去世整一个月那天,我独自进城,“旧地重游”。——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在追寻什么。我乘公共汽车到灯市东口。路口西南角上原来有家香侬餐厅,现已改为北京蒙娜丽莎婚纱摄影东单旗舰店。母亲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们曾经在此为她祝寿,当时拍的照片我还留着。沿东单北大街南行,协和医院对面,原是上海餐馆雪苑,现已改为红石头餐厅。母亲和我曾经多次来这里吃饭,常点的菜是响油鳝糊和油爆河虾,还记得有位倒茶的女服务员,人已不算年轻,上海口音,说话挺客气的。再向前走路过大华电影院,这是母亲和我常看电影的地方,如今装修改造,暂停营业。
我在东单乘公共汽车,到南池子下来。我曾在日记里写道:“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陪母亲去王府井,沿皇城根、菖蒲河走到天安门,在起士林吃饭。”母亲就给姐姐写信说:
“原来的旧河道废了,上面盖了房子,都是那么又低又矮的平民住房,现在推了,重新开通河道,再建公园。配合那红墙,里面建了一排古建筑,这公园是值得一游的。”
此番我重访菖蒲河公园,南池子大街路西的一半已经关闭;路东的一半两头亦挡以铁栏,然错有缺口,可以穿行。里面人迹稀少,花草全无,景色萧疏。问环卫工人,则云冬天谁还会来,西边“十一”前就关了。
我一直走到东华门大街。这天晚上,我和大哥一起在华龙街的起士林吃饭。此处亦已面目全非,北面的开放式走廊不见了,店门改了位置,店内也添设了洗手间。问服务员,说是前年春天改造的。母亲的信中记下了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那次点的菜:
“沙拉,奶油汤,方方吃炸鸡卷,我吃的罐焖牛肉,又吃了栗子粉。奶油栗子粉多年未吃了,栗子粉略嫌粗点,奶油是那种带点酸味的,很好吃。”
又说:
“我们在华龙街起士林吃的西餐,让人还想再去。”
大哥和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回忆起母亲的许多往事。
几天后我又路过朝阳门北小街的楼外楼,正是吃饭时候,里面却黑灯瞎火。这也曾是母亲和我常来的地方。几年前换了招牌叫哨兵海鲜,现在干脆关张了。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来,查母亲的信是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五日,那天饭刚吃到一半,突然天色如墨,街上车辆、行人幢幢有如梦寐,继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当时母亲望着窗外的那种既惊异又忻幸的表情,此刻犹在我的眼前,鲜明真切极了。
汉语有个新词叫“地标”,也许可以说,还有一种属于个人的“记忆地标”或“情感地标”。
我发现,与母亲相关、与她和我那一段共同经历相关的这种“地标”,已经陆续不复存在。它们甚至先于母亲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了。
说得夸张一点就是,母亲虽然离开并不很久,但我感觉她曾经所属的那个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了。
和母亲一起看DVD
母亲留下一份目录,列着她生病以后所看的DVD,共计二十三页。母亲是个影迷。言谈之中,常常忆起早年看电影之事。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陪母亲看电影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能想起来的是“文革”后重映《龙须沟》,看到一半母亲和我都哭起来——我们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家里住的房子,下大雨时到处漏水的惨状。现在那一幕还在我的眼前:纸糊的顶棚上鼓起一个个大包,如不赶紧捅个窟窿泄下积水,那么整张纸都掉落下来了。再就是母亲一连到电影院看了七遍日本电影《追捕》,其中至少有五遍是和我一起去的,这件事她晚年还常常提到。当初公映此片删节颇多,后来我买到完整版的DVD,可惜没有给母亲再放一遍。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先后举办了英国、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瑞典和美国的电影回顾展,地点多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偶尔也在北展剧场或人民剧场。母亲和我都去看了。我还记得那次法国电影回顾展,同时还有美国电影周,母亲和我两边都不愿舍弃,有一天早、中、晚跑了三个地方,看了六部电影。
我们搬到望京后,起初她还大老远地进城去看电影。在给姐姐的信中说:
“我去大华看电影了,现在离退休老人都半价,花了十元,看了黎明、张曼玉的《甜蜜蜜》,很好看,也是得奖的。有了这半价,我每星期进城就可以看电影了,不然我这个影迷一直没怎么看电影。”
后来母亲就不大出去看电影了。她在给姐姐的信中又说:
“我已有过去看电影的辉煌成果,现在也得服老,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在每天吃过晚饭之后看DVD了。母亲不看国产电视剧,曾评论道:
“编电视剧的没有生活,没有体会,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凭空一想写出来骗人,可笑,没法看,所以我只有等方方晚上放些好的有价值的电影给我看。”
看DVD这事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即使在母亲生病后,除了她几次住院,几乎未曾中断。我晚上偶尔外出,也尽早赶回去,无论多晚,都要看一张碟。母亲则坐在沙发上看书,等我回来。说来我也不知道是她陪我看,还是我陪她看,反正我努力挑选她可能喜欢看的,至少是能够看的;有时候我同时找出几张请她取舍,她总是说:看哪个都成,反正都得看。母亲在信中说:
“我们看碟,有时一部,有时两部,这是方方最高兴的事,我当然奉陪,不看也没事可干。”
“我认为好的电影,会在看完后左思右想,影响睡眠,至于我认为一般或很差的电影,看过后就不记得了,不进脑中。”
母亲看电影,可以接受好人有坏结局,也就是一般的悲剧;但不大接受坏人有好结局,如某些黑色电影。这反映了她的思想,也折射了她的人生。
我们看DVD,本来是在晚饭后;母亲病重不能看书,就对我说,白天也看个电影罢。那时她已经不能久坐,在她的座位上加个棉垫子,前面放着助步器让她扶住,片子放到一半,还要搀她站起来拍拍身子。这样一直坚持到她住院的前一天。那晚上看的是荷兰导演本桑伯加特的《暴风雨》。因为第二天要早起,我看这片子只有九十六分钟,算是短的,就挑了它。没想到竟是母亲一生中所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了。
母亲去世后,有一回我寻找一张DVD,从柜子里逐一抽出之际,忽然想起这些都是与母亲一起看过的,我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当时她喜欢与否,正所谓“睹物思人”——这种“思”鲜明、强烈到有种将人逼至角落之感,简直难以承受。这与整理母亲曾经读过的书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
母亲为我编选文集
母亲的遗物中有一小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文章的一些标题,这是她为我编选“三十年集”时所做的记录。出版社编辑来电话约稿,正赶上我看见母亲做脑部核磁共振的报告,显示再次发生肿瘤转移,我有关她病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希望遂告破灭,就想让她做点什么留个纪念——虽然我并未对她讲明。
母亲前后花了五天时间编选的这本书,后来取名“河东辑”。她在日记中写道:
“方方应邀编一本三十年集,他说让我协助他选他的文章,我有能力吗?试试吧。”
“上午我还在看方方在他的著作中挑出的文章,再让我精选一遍,我看重这个工作,或许经我再挑选,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方方继续让我代选他的文章,我已弄好,不知如何。我想他所以让我帮助他编此书,也是要给我增加自信力,让我觉得自己还能为孩子做些事情,打发掉我因病而带来的悲观。他用心良苦。”
过了半年,出版社寄来校样。母亲在日记里写道:
“送快递来了,是方方的三十年集,好重,序言中感谢我帮他编集,祝我健康长寿,我看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之后编辑不断告诉我书快印出来了,但就是总也印不出来。整整一年过去,终于拿到样书,而母亲已经陷入昏迷了。有一天因为使用激素稍稍清醒,我把书举到她的眼前,对她说,本来我想请您签个名字的。她带点歉意地说,怎么签呢。我这愿望也就没能实现。后来我写文章说,西谚有云“迟做总比不做好”,可是有的时候,迟做与不做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母亲的写作
母亲一直有从事写作的愿望。
在她的遗物中有个纸盒子,放着她的一些文稿,包括一小册新诗,两个完整的短篇小说以及四五篇小说的残稿。八十年代初期,母亲用“沉苏”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过几首诗,那些杂志她一直留着。还有一个本子,抄着母亲写的一篇游记,共三十七页。母亲在一九八三年的日记里就说:
“翻出八〇年我游杭州的信,读了一封,很有意思,我想去掉不必要的,把这些信抄在一个本子上,以后翻翻也可重温南游的情景。”
十八年后,她给姐姐写信说:
“还整理了八〇年去杭州游玩给你和方方写的信,共廿封,将来订成册,也算留给你们的纪念。”
我还找到她三十多年前写给我的几封信。其中一封信里说:
“你今天走后,我生起炉子,就开始写我的短篇,一直写到晚上十点三刻,完成了。题目叫‘空壳’,共三十页,即六千二百字,当然太长了,等你回来砍吧。如果这篇能使你稍为有点心动,那将是我最大的安慰。好,等你回来。”
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我已不记得我是如何回应的了,只怕当时不够热情,扫了母亲的兴致。这篇小说保存了下来,取材于她自己“文革”中的亲身经历。
那个纸盒里还有一张剪报,是母亲搬来城外不久,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署名还是“沉苏”。母亲给姐姐写信提到此事:
“我写了一篇东西。是因方方不适合给《北京晚报》发东西,他写得太深,不大合乎那报纸的口味,约稿的人说让他随便写点,可以用别人名字,说只要妈妈(指我)看得懂即成。方方说那还不如让我妈写呢。这样我就自告奋勇写了一篇。方方说写得不错,只是短点,也成了。编辑叫王东,打电话来夸奖说比方方写得好,这怎么可能呢。”
这里是她所写的全文:
短暂的视野
儿子在城区的边缘买了房子。我随着搬来之后,陆续有亲戚朋友来访。除夸奖房间的装饰布置外,最满意的还是从宽敞明亮的窗户向外眺望,都称赞视野很好。有的还总结说:“买房就是要挑视野开阔的。”大家对我们新居的肯定,多少冲淡了当初为装修搬迁花去的劳累之苦,我也就尽情享受视野带给我的欢乐。
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见太阳升起来了,白云飘在蓝天,大片树林直抵天边,远山隐约一脉。夜晚窗外挂着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去年冬天初雪之后,大地白茫茫的,从来没有过的寂静,我仿佛看见雪地里有只狼缓缓而行。这种近乎犯傻的浮想联翩,给我很大乐趣。虽然将近老耄之年才住上这样的房子,我还是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视野的赏心悦目竟如此短暂。好像顷刻之间,原来我们视野里的大片荒地就变成日夜喧腾的工地了。对着我们的北窗,已经矗立起一幢二十多层的高楼——当然现在还只是个水泥骨架而已,我这才觉得楼要光是水泥骨架实在太难看了。东窗外接着在为另几幢高楼打地基,整天轰隆轰隆吵个不停。当然在这种边缘地方是没有人来测分贝的。别说白天的视野了,晚上睡觉也成为难事。我想起当初买房时对视野的考虑,原来是一种短视。如果挑视野不那么好的,也就是说,跟别的楼挨得比较紧的,可能反倒要舒服得多。我想还是把这个经验或者说教训告诉别人吧。
儿子安慰说:“要不多盖些楼,这儿怎么能繁荣呢,是不是,妈妈?”当然是这样了,那就忍耐,盼望,直到繁荣的到来吧。到那时我也就不会想到有什么狼了。
多年以后重读母亲的文章,觉得她的兴致、寄托,她的寂寞,她对声音的敏感,都表现出来了。只是所提到窗外的几幢楼,已经都很老旧了。
(摘自《惜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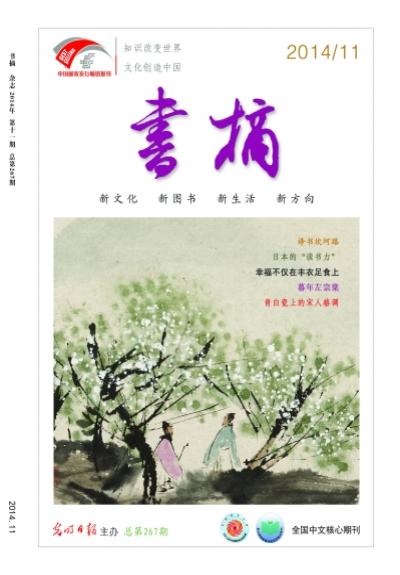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