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庶民社会的觉醒、崛起,其实是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变化,是改革开放步入更深层次的表征。物质文明提升,势必催动、激活精神文明。倘若指望一边繁荣经济、改善生活条件,一边使人的意识和精神状态维持不变,只能是一厢情愿,世间并无此事。反之,仓廪足、知荣辱,精神随物质而变,或物质变精神,这规律却是一定的。
但庶民社会觉醒,不像精英阶层思想运动那样,以边缘清晰、完整的事件或激烈、突出的意识形态冲撞为表现形式,而诉诸诸多零散、无规则现象。这些现象,彼此往往并无直接关联,有时一夜之间,忽如其来。我们观察的着眼点,不在单个现象,而在各种现象的齐发并现、纷至沓来,从中确定一个时间窗口。
我们认为,在中国,公众精神意识趋于活跃的第一个时间窗口是1986年。简单来讲,经历七年改革开放,物质生活的改变,已转化出能量,去刺激或催发人民精神面貌发生变化;同时,经过一些“反复”,清污运动铩羽,卫道势力落于下风,社会精神先抑后扬,勃勃欲发。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未能紧跟物质文明的步伐,而遭遇某种瓶颈状态,那么可以说,1986年已经来到突破瓶颈的前夜。
1
1986年,庶民社会甚至曾以一场庆典,来宣告他们在文化上的崛起。
有关这件事,要从两个背景说起。一是流行乐在中国的坎坷经历,一是1985年美国大牌歌星的一次盛举。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歌、民乐、戏曲以及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整理、开发和利用,十分系统而有深度。与此同时,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对西方古典音乐(即印象派之前)亦能容纳,将交响乐团、歌剧院的建设,置于国家计划之内,并通过音乐学院的专业教育培养人才。不过 “文革”开始后古典音乐作为“封资修”遭到禁止。唯一自新中国成立起即遭摈弃的,是流行乐。当时有“靡靡之音”一词。
改革开放后,绝迹的事物,纷然重现,流行音乐以其近迩人情,动静最早。邓丽君的流入,令三十年来中国大陆音乐闪现新的一角——当时,没有或不愿采用“流行乐”概念,而略带不屑地以“通俗歌曲”相称。
邓丽君歌曲,只能在民间流传,官媒不但不予认可,对境内加以借鉴的歌者还大事挞伐(例如,有文章竟将“气声”唱技解为色情意味)。这样的舆论,一直持续到清污运动。
1985年,趁着清污夭折,局面终于为之一变,标志是涌现一批职业歌手且各自形成一定市场——他们便是共和国第一代“歌星”。流行乐时代,似乎只欠一个揭幕式。
天遂人愿,偏在这时美国流行乐坛发生一桩事,既送来灵感,也提供了可以酌取的范式。
话说不久之前,非洲大陆爆发严重饥荒,成千上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举世震惊。在美国,迈克尔·杰克逊睹此惨状,1985年初首倡流行音乐家们携手合作,灌制唱片和举行赈灾义演,以其收入捐献灾民。此议甫出,即为数十位当今顶尖歌手响应。杰克逊亲自创作We are the World,五十名极负盛名、腰缠万贯的歌星加盟,共同录成单曲出版,继而献演于“拯救生命”大型义唱。历来被目为颓废、放荡、玩世不恭的摇滚歌星们,以最严肃的姿态出现,世人为之刮目、感动非常。整个活动取得巨大成功,筹集善款逾五千万美元,而We are the World从此传遍世界,成为流行音乐史不朽之作。
义举轰动全球,各地纷起效仿。在台湾,罗大佑于同年写出《明天会更好》,聚集六十余艺人共唱,也流传甚广,大放硕彩,至今不衰。
一远一近两首作品,对境内流行乐坛都有广泛触动。中国流行乐界在关注着迈克尔·杰克逊、罗大佑们的作品与行动,有所思考和议论。转至翌年,适逢联合国以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新生的大陆流行乐界意识到,可以此为主题和契机做点什么,补上去年中国声音的缺席。
一番探讨后,曲作者郭峰和词作者陈哲等合作,写成《让世界充满爱》。旋律有东方的宁静空灵,精神内容则明显属于普世价值,熟悉We are the World的听者,很容易发现来自后者的流韵。
演唱会申请,出人意料获文化部批准。据说,“在此之前,有关部门曾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而此番却将有超过百名歌星同台。郭峰事后说:“这是文化部门首次对流行音乐破例。”
演唱会讴歌社会责任感和爱心,这与“主旋”相协调,然而毕竟是流行乐演出,很难避免出现在令当时“主旋”感到异端另类的举止、形象或场景。当唱到《让世界充满爱》的第三部分时,站在第三排的崔健出人意料地在现场走起了“太空步”;霹雳舞演员陶金,从头至尾在一旁扭来扭去;孙国庆则留了个特别有意思的朋克头。
这些固然有点出格,但尚不至于令人不快。等到崔健开始演唱那首成名作《一无所有》,主席台上气氛真正凝重起来。二十年后,有媒体复原当时的现场经过:
5月9日,北京工体,……最后一个无名小子上台。他穿了一件显长的黄军装,敞胸露怀,里面的白衬衫随意翻到了外面,像脖子搭了条毛巾;白裤管一高一低,一只裤脚嵌在袜子里,似乎没来得及拽出来。……演唱会的观众席上,有不少官员,中顾委委员荣高棠、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其中不少人当即拂袖而去。
中国摇滚乐的开篇之作,就这样在人们并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而且当着众多高级官员的面。
“一无所有”的字眼,当时很难不让人侧目。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青年人人具有崇高理想、远大志向,怎么能说“一无所有”呢?再者,那个年代报章上从来是“跟党走”,冷不丁崔健居然吼了声“跟我走”,一时间怎不令人勃然变色,以为这蓬头垢面的家伙吃了豹子胆。就此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崔健被视做洪水猛兽禁在官媒之外,不无道理。
从严格规定流行乐三人以上不得同台,到一跃而为“百名歌星演唱会”,其间具体如何有此变化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文化部经过一番犹豫,放行《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准其使用工体。但恐怕在审查环节上有所疏漏,致崔健混迹其间、借壳下蛋,携《一无所有》亮相,使摇滚乐挤入工体。这当中,颇显出历史的尴尬:“放”与“不放”,皆难两全。粗粝、不合“美感”的《一无所有》,与其说是歌乐,不如说是号叫。当晚一幕,可谓斯文扫地。忽然间,峨冠博带幻作赤膊光头,妙相庄严变成撒泼放肆。自兹往后,江湖气、草根相以及原始、野性、剽悍气质,即开始奔突于文化,不仅“西北风”在流行歌坛一刮好几年,连电影《红高粱》(1987年出品)镜头画面也分明浸染了《一无所有》的风味。
在美国,摇滚是蓝领对于白领生命状态的排拒;在中国,则是庶民对于雅驯文化的出走。这种细微区别,只有细细体会方能捕捉和领会。不雅,是对“美”的摒弃;不驯,是对“规范”的抵制。以往中国文化,以既美且驯为理想,如不能美,至少也须合乎于驯。庶民文化,由于不雅不驯,历来不能登堂入室。无论如何,工体之夜堪称一座大众文化里程碑。是夜,流行乐、摇滚乐双双亮相,就此风靡。不知不觉中,原本注重教育功能、从来神情庄重高高在上的舞台,开始了世俗化、平民化的转变。
2
以上所述,不约而同指向于一点:改革开放七年后,庶民社会在精神和文化上终于呈现爆发态势。
在中国,历来谈到精神思想的变迁,民众似乎都可忽略不计。他们终其一生,除却劳作、思欲只及温饱。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与其说是一种歧视,毋如说是现实写照——力尽筋疲,犹难奉给,乃至不偿其费,哪有余力顾及精神天地,所以“治于人”是必然的。我们从古代看下来,一直看到现代和不久以前的当代社会,民众在精神思想上无时无刻不处在被给予、被书写、被启蒙、被教导的地位。毛泽东《讲话》要知识分子以工农为师,似乎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实际则是以此使文化领导权易手,从知识分子那里移诸革命意识形态之手;“文革”十年,“人民”一词在字面上至高无上,实际却在精神思想上大搞愚民、役民。
改革开放萌动之初,即以“思想解放”为口号。而究竟是否做到这一点,最终不是看政治层面和知识分子层面,要看普通百姓层面。如民众在精神上自主性不能确立,“思想解放”在中国就缺乏实质意义,到头来仍无非是延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关系。
应该说,到1986年,民众自我意识觉醒和价值独立的趋势,已经释放出明显信号。改革开放政策,所改变的不是一部分人生活,而是全社会性的,几乎人人受益。正因此,广大人民对生活的期待与认识普遍提升,生命意识逐渐越出生计之外,追求尊严、充实、愉悦等精神价值。拿1986年和改革之始的1978年比,明显的变化是,精神生活中来自民众的声音和表达变得格外突出和重要。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基本属于“上层话语”,西单墙乃是精英和知识分子所为;普通民众除少数特殊人群(如含冤者、知青等),对于精神思想问题甚少有所关注、参与。1986年截然不同,普通民众精神力大增,从个性意识、标新立异到价值自主判断、不以主流或精英的是非为是非,趋向十分明显。进一步比较我们还发现,1986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相对平淡,反倒是庶民社会躁动不安,表现欲强劲,每有惊人之举。
欲知这一时刻意义若何,不妨看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怎样大行其道,与官方、知识分子价值观分庭抗礼,三分天下有其一;以及新世纪以降,又怎样进而风卷残云,不单不复仰人鼻息,转以铺天盖地之势令庙堂文化向它折腰——譬如央视春晚对赵本山团队的过度依赖、“文坛”对市场化作家示好、郭德纲公然睥睨主流媒体……即以1986年为界,文化之变庶可谓改天换地。
当然,庶民文化呈决堤之势,也有负面性。如今,精致的文化样式、品种基本上全线溃败。“三俗”之称虽从政治角度提出,但验之于客观实际也不得谓之捕风捉影。即如笔者,主张对庶民文化的蓬勃兴盛,着眼于大历史而给予理性的对待,但在若干具体现象上,论以个人趣味却难抱好感。
本文以庶民社会及其文化崛起为1986年特色,是着眼于其历史作用,不含将它突出为“主潮”之意。如果1986年只是从一种文化霸权去往另一种文化霸权,则中国文化的前景并无值得欣喜之处。好在实际并非如此。考之于现实,小众文化、亚文化在中国虽未蓬蓬勃勃、蔚然成风,但相较从前却可以说从无到有、水落石出,尤其互联网普及以来,独特的价值认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业缘代际、性别、爱好、学术、思想、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形成一个个精神群落。而这种情形的萌芽,在1986年已有清晰表现。
(摘自《典型年度:当代中国的思想轨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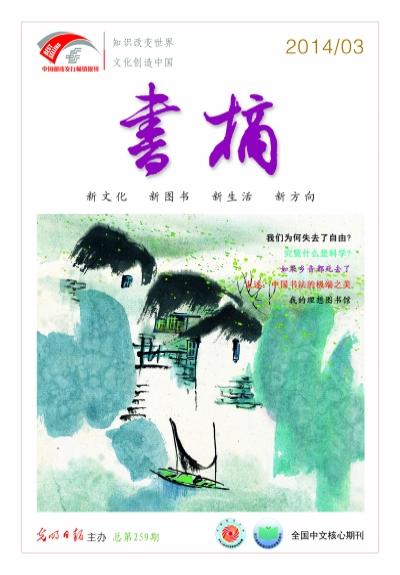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