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的忌日了。一晃六年过去,六年来,每当想起父亲,我就觉得很沉重,一种对不起他老人家,而又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痛楚猛烈袭来,父亲对我的挚爱与我对父亲的孝心,真是天壤之别。
那一天,办完父亲的丧事,我和姐姐、弟弟不约而同地回到父亲的卧室,翻检父亲的遗物。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既是对父亲的眷恋——父亲虽然去了,但他生前所用的物品,不也是父亲的一部分吗?又是想从中找一件父亲常用的东西作为终生的纪念。明天,我们姐弟即将东南西北,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祭奠父亲呢?
我一眼看到衣箱里的一个茅台酒瓶子。我拿过来,眼里顿时涌满泪水。这个酒瓶子我太熟悉了。这是我大学毕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给父亲买的礼物。父亲爱喝酒,但从不买高级酒,也买不起高级酒。尤其是母亲去世后,家境困难,一条黄瓜就是下酒的菜。记得茅台酒当时是八元四角钱一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很贵的价钱了,一般人不买。我早就计划好了,等我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买一瓶茅台酒。
没想到这个酒瓶子父亲一直留到现在;22年过去了,瓶子旧了,商标也变了颜色,父亲依然保存着。想到这些,我的泪水不能控制。儿子对父亲的一点点好处,父亲是如此珍重!父亲对儿子的满腔期望,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抚育,可以用什么衡量?儿子又如何报答得了呢?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因为工作忙,很少回老家。因为老家在铁路线上,有时外出开会,散会后,中途下车,回家看看老父亲。我记得在家住得最长的一次是1987年的中秋节,总共在家住了36个小时。那年父亲已经74岁,患过肝炎刚从医院出院。过去父亲住的楼房没有暖气,是弟弟自己装的土暖气,烧不太热,在房间里穿着棉衣棉鞋还缩手缩脚。这次回去,经过弟弟的努力,父亲的单位照顾他年老体弱,又刚刚病好,给他调了有暖气的楼房。外面冰雪覆盖,室内温暖如春,父亲只穿件薄毛衣,舒坦得很。我很为父亲终于住上了暖融融的房子而高兴。但看到刚出院的父亲脸色苍白,弱不禁风,酒也戒了,烟也不抽了,我心里放不下。想多住一两天,又怕耽误了工作。父亲看出我的为难?笑着对我说:“回去吧,我这不是挺好吗?回去干工作去。”第二天,我走了,弟弟替我提着提包。父亲也穿好了衣服要去送我。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外面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着了凉怎么办?劝阻再三,父亲同意不去送我。没想到,我和弟弟刚登上站台,还没有放下提包,父亲便走了过来。倒背着手,朝我和弟弟微笑着。那得意的样子,仿佛在说:怎么样,不比你们走得慢吧?啊,我顿时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想起了《背影》中父亲的形象。普天下的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的忘我,都是这样的挚爱无边啊。那是父亲最后一次送我。几个月后,他就又一次住院,终于没能从医院出来。
我手里还保存着父亲的另一件遗物。这是一个图书馆的借阅证。六年来,每当我看到这个借阅证时,惭愧、不安和负疚便一起袭来。那个借阅证已经很旧,在借还日期栏目里密密麻麻、一行接一行,几乎快写满了。细看借还时间,多半是今天借,明天还,最长的间隔是三天。几乎天天跑图书馆,每天读一本书。而在这个借阅证上记载的最后一次还书时间恰恰是生病住院前几天,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每天奔走于家与图书馆之间,我怎能不惭愧?
除了惭愧,我还有一种负疚感。父亲特别爱读书。60岁离休之后,《英语900句》传入中国,他得到一本,整天不离身,诵读、默念,像一个中学生那样用功。随后,又开始学朝语,让我吃惊不小。一次看到他枕边有一本《朝鲜语读本》,很奇怪,问他这样大年纪了,为什么还学朝鲜语?他笑笑,说:可以帮助理解日语。
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偶然得到欧·根室的《非洲内幕》,父亲爱不释手,几次对我说,这样的书看了视野开阔。书前的目录没有了,书后也缺了几页,父亲先是按照书的页码、书中的标题自己编了一份目录,粘在书前;后来又托人从长春借来一本完整的《非洲内幕》,将缺的几页用稿纸抄下来,又把稿纸裁成书页一样大小,补在书后。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是做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未见父亲有多么高兴,他唯一的嘱咐是:以后有好看的书寄点来。我因为忙于杂务,很少给父亲寄书。最近翻检父亲给我的书信,先前几乎每封信都说,如有便寄点可看的书来。后来,说的就很少了。今天想想,这是父亲向我提出的唯一的要求,而又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唯一有条件满足父亲的一件事,我却没能去做。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父亲病重住院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内心就不能平静。父亲病重,一躺40天,我和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利用“五一”假期回去看他。他十分高兴。我们回去前,他吞咽困难,一天吃不下一碗稀饭。体重只剩七十多斤。我们回去后,陪伴着他,和他聊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父亲居然缓了过来,渐渐地一顿饭可以吃一小碗馄饨,或者一小碗片汤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40天过去了,当地的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我和弟弟设法给他转院。父亲没有提任何要求,一任我们安排,实际上他是希望跟着我到北京的。也许是为了治病,也许是为了在离开我们之前,能和我在一起住一段日子。但当时我考虑得非常实际。我实在为难了。北京的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到了北京我有能力让父亲立即住进医院吗?我住的是平房,没有卫生间,不论刮风下雨上厕所都要到胡同里的公厕。当时父亲体重只剩下七十多斤,每天需要打点滴输葡萄糖,不要说一个月住不进医院,就是一周,怎么办呢?这时朋友鼎力相助,为我在长春市联系到一家医院。权衡利弊,我下决心把父亲送到长春的医院。我因为急着回单位上班,没有送父亲去医院,朋友从医院请来救护车把父亲接走。那一天,我看着远去的汽车,怎么会想到这是和父亲最后的一面呢?父亲去世后,每想到当初住院的情景,我都心如刀割。我虽然用种种解释为自己辩白,但我从来没有心安过,尤其想到父亲把自己的愿望存在心里,怕儿子为难,我心里就更加沉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勇气把内心如实托出,一直为自己开脱。实际上我是不肯承认自己面对困难的无能,不敢承认担心父亲来北京自己托人情、找医院,东奔西走而无可奈何的忧虑。今天,当我这样想,这样请父亲宽恕时,我心里终于好受一些了。
六年过去了,六年的痛苦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一生并不只是工作,人生还有那么多真挚的东西,那么多动人的感情,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能够让我们活得好、工作得好的动力。父亲的一生没有壮烈的场面,也没有多少得意的时刻,任何地方也留不下他的名字,但父亲的去世,却最后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就是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珍惜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
(摘自《云深不知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定价:36.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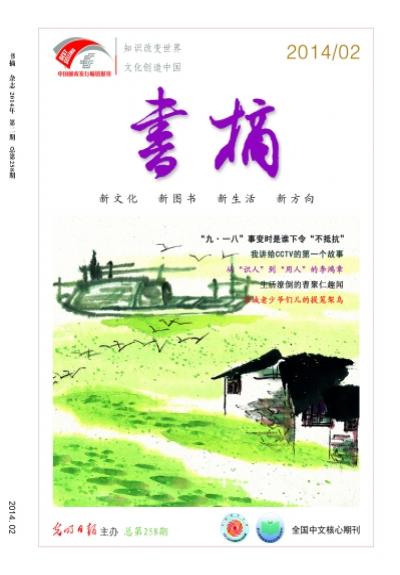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