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台北市的青田街七巷六号。它是父亲来台的寓所,从民国三十四年底来台之后,父亲没有换过住所,一直在此,到他去世,一共在此生活了三十四年。
寓所进门的左边,是客厅,门做得特别宽,两扇合而为一。只这一间房间,一共有四个可以出入的门户,一通玄关、一通餐厅、一通书房、一通花坛,如今通书房的门已经不见了,代替的是用合板刷了白漆的假墙。但设计者足立教授用心良苦,也看得出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讲究的人。
客厅也可以作为生活的起居之用,这间房间的使用时间不仅很长,也很频繁。要是一家子和和气气相与,可以让这一间屋子充满了家庭的温暖,可惜我们家独缺这一味,长年都是父亲一人当作延伸出来的书房,习惯上是我们小孩子的禁地。后来见识到许多教授的住宅,大多也是把客厅当作了书房用。他们客人不会多,就是有,也用不着依严格的礼仪接待,书籍、未完成的论述,还有许多标本、显微镜片等等四处散落的客厅,也许更具风格。
长年的穷,无法让父亲添置新的家具。客厅对着巷子的窗子是西式设计,有着长长菱形窗框,大方又透光。窗台可以有点儿摆设。这间客厅的墙上挂着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列窗子跟窗台上方,挂着一幅孔子问礼老子图、一幅汉代石刻的原拓片,现在也不知去向了,连什么时候不见的,我这个离家太早的晚辈,也是不得而知了。早年的客人当中,李杏邨教授是常客,他比父亲年轻,深通佛学,并收藏许多古代汉砖石刻拓片跟原石。这一件原拓,应当是他送给父亲的礼物。
要说父亲生活上有一点难得的情趣,便是他每天早上在花坛上做运动,先是缓缓吐纳,接着打一趟太极拳,我从屋里姊姊的那一间小房间,看得见父亲打太极的身段,他打得云里雾里一般,比什么舞蹈都好看。
书房对于一位大学教授来说,大约六个榻榻米,面对院子,只有一扇窗,背后也有窗,通到长廊,前后的景观都很好。这真是小了点儿,难道最初的足立教授不读书吗?相信未必。小时候,家中无处不是书,最醒目的,便是在走廊上面,也用桧木架上了长长一列书架子。书房隔壁的小房间,也就是最初齐邦媛、后来是“教育部”蒋建白司长、接着是姊姊一直住到出国的小房间,墙上也装了从地面直通到天花板的书架。在长廊一侧的阳光花房,后来没有再养花了,却在两旁放着好大的书柜。厨房前走廊边的柜子里,也都是书。便是如此,父亲在台大研究室的书,远远超过家里的藏书。后来他把在研究室的书,全都捐给台大,最后点交也没有任何仪式,但是那一年夏天,是我天天去开研究室的门,让校方的人进来整理清点,那个时候父亲在欧洲讲学做研究。记得有十万册以上。想来足立教授也是在研究室读书,一位教授的研究室要是明窗净几,十分幽雅,我总觉得这样的教授靠不住。但是在今天校园里,这样凉快的研究室倒真不少。我见识过摆满葡萄酒跟各色茶叶的研究室,感怀万千。
书房对着前院的花坛,直可望见大部分的花园。书桌就在窗前,但是右侧放置了一个大大的桧木玻璃窗书柜,空间就更小了。那个玻璃书柜有上下两层,可分可合,上层是放书的,下层是抽屉,两层中间有一片桧木原木的隔板,有一对铜质拉手,可以把板子拉出来,很顺手。一拉就能拉出整个书柜的深度,至少有两尺宽,也可作书桌用,用完了又可以推回去,恢复了原先的平平整整。里面放的不一定只有父亲专业的地质学方面的书,也有艺术方面、哲学方面、历史方面等等的书,有一部不完全的日文版论语注本,全部都是汉字。从那个书架上,我读到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有孟子。这些书当初也不知来历如何,读起来似懂非懂,然而读得津津有味,小时读古书,只觉得声调悠扬,特别是唐宋八大家,常常不知不觉地诵读出声。后来确定,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个个都通音韵,先有了音乐家的条件,然后方能作为一个学者还是作家。我不知不觉地享受到了读书之美,非常幸运。可见许多书本最初是用来享受,而非一定要理解,考试制度让大家忘记了读书首先可以享受,乃一大错误,一大非常不幸的错误。
科学的书当然不少,我也爱读,特别爱读那两巨册的简易牛津大字典。要说是读十分夸大,我是爱看里面的插图,千奇百怪的;也爱看里面的人像,风格形象各自不同。父亲直到去世大概也不知道,我不言不语地从他的书架上翻阅了多少他的藏书,而且,养成了一生爱读书爱到不可自拔的习惯。现在已经年近古稀,一眼渐眇,依然嗜读如狂。
记忆中,在早年,父亲的书写工具有三种,其一是打字机。他有一台老牌的“皇家”打字机,英国制,看来是他早在当留学生时代就开始用到了后来。据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年,他们头一次在南京见面,他见到了这位初识的朋友,一手提了个箱子,一手提着半打酒瓶。他就想,这大概是个很讲究享乐的纨绔子弟,那个手提的箱子,应该是一台手摇留声机,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玩意儿。另外一手提的自然是酒了。又听歌曲又喝酒,这个人在他的第一眼中,不会有很高的评价。后来证实,那个箱子,就是跟着他几十年的打字机。至于所谓的酒,却是汽水,因为父亲怕热,刚刚买了几瓶汽水,打算也可以用来与新朋友同享。
书房后来跟客厅一元化,父亲进进出出次数最多的门,就是书房通客厅的那一扇现在不见了的门。客厅毕竟敞亮得多,我们家一直没有装冷气,也没有能力装冷气。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在家享受过冷气。台湾的长夏,让原本就怕热的父亲很受不了,他就只穿背心工作,要是热极,他也会打赤膊,但是很少见。在客厅的矮茶几上放着打字机,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专注地打着他的论文,没日没夜的。客厅也跟着他的研究发展愈来愈挤促。原本一张长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中间一个茶几,只要放得下资料,也都堆得高高满满。
父亲一直缺钱,可是,不知道他是怎么为自己节俭而省下来一笔钱,购置了一个好大的、直径约有一米的地球仪,这个客厅,看来就像全宇宙,我想对父亲的意义也差不多。他是发现地球自远古曾经有过若干次赤道改变的学者,因此,这个地球仪就很特别,没有一般地球仪的固定转轴,是放在一个圆形的架子里,地球可以整个地从架子里拿起来,架子的周围有经纬线的刻度,地球仪的经纬线,是可随着这个地球仪的变动而变动的。这还不够,父亲又定制了一个透明的、半圆形、刚刚好可以套在地球仪上的套子,套子上也以黑笔画好了经纬线,可以以他估算理解的远古南北极为标准,把套子套上去,也就因此可以推断在什么时期的地球的什么地方,该是什么温度什么气候。地球仪是以薄钢片为材质,要制作得非常精准,否则会差之毫厘去以千里。我这个外行人常常想,也许这一个不同寻常的地球仪,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惜的是,随着父亲的老去,这个地球仪后来也变得锈痕斑斑,形迹漫漶,终于成了不可辨识的远古了。
父亲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安静一点儿,走过他有形的学术世界时,也都放轻脚步,但我却是忍不住地多瞄一眼。只见父亲穿着白色的汗衫跟短裤,在客厅一大堆看来杂乱无比的书籍跟资料里,埋身其中。父亲戴着老花眼镜,也许研究做得顺利了,他神采焕然地对着打字机,自顾自地抖抖腿、哼哼不成调的歌曲,要是仔细听,应该就是他一生只会哼的唯一的一首歌《满江红》,那是对日抗战时在大后方陪都重庆流行一时的歌曲,他们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没有不会唱的。父亲会不会唱“国歌”,我很不确定,虽然确定他非常爱国。父亲有时候也许要思考一下问题,就会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脚下一双拖鞋踢踢拖拖,声闻全户,无法预料他要走多少趟,然而他旁若无人,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小孩子有时宁愿绕道而过,少去惹他找骂。
客厅的景观自然是屋里各房间当中最好的,父亲有的时候也会在窗前小立,很难判断他是在欣赏院子里的花与树,还是在思考着他的研究。不过这样的景况不常见,见到的,都是他不眠不休地工作。
后来父亲干脆把床搬到了客厅,就放在花坛边上的那一面窗子旁边。他累了躺在床上,侧身就可以欣赏花朵。我在初中要考高中的那一阵,父亲要我在客厅读书准备联考。他不在家的时候,我读书累了,也会在他的床上躺一会儿,觉得跟父亲好像更接近了一点儿。父亲回家总是在晚上,常常都在晚餐之后,他也总是买回一些水果,我们父子两个同吃,那是亲子难得融洽相处的时光。他买那么一点水果,要花的那一点钱大概也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把类似橘子什么的,藏在书桌抽屉里,怕别的孩子见到了偷吃,为的是留给我吃。也许留得太久,常常都不怎么好吃了。
最让我怀念的是父亲回家甚晚,也许都已到了半夜,我在榻榻米的房间睡觉,是跟客厅成对角线的两头那么远的距离,但他一回来我一定知道,怎么样都要起身,去上一趟厕所,不管有尿还是没有尿。父亲就要我到客厅来,当时也是他的卧房,只开着台灯,他取出刚刚买的水果,父子二人在深夜同吃,清脆的咀嚼声中,我们拥有秘密的温情。只那么短暂的一两个月,也就是我与父亲的一生一世,如今我想。
父亲一生没有抽过半口烟,这是他亲自跟我说过的。他虽然酒量了得,也很少饮酒,因此家里的空气总是清新宜人。家里的客厅,最醒目的就是父亲跟他那少见的巨大的地球仪了。他的鼻梁上架着厚厚的老花眼镜,时而在此,时而在彼,绕着大大的地球仪活动,要是让超现实主义大师杜尚来画,可以在地球仪四周画上许多个远近高低不同的父亲。
父亲去世之前,卧房是他原先的书房。我是从他的老书房带走了他去了医院,却永远没有回头。至今我依然常常想,要是他最后是从客厅离开的,心情会不会有点不同?病到那个样了,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多余的吧?但有一点我非常确定,要是早知道那一趟把他带去医院,他就再也不会回来,我怎么说都要让他亲自看看这个家,这个庭院的每一处,我要让他触摸到每一处他想要摸的东西,每一株他亲手栽植的树木。我一定不会先叫了计程车,就把他一阵风也似的,给带到他当年接收的台大医院去。每次回想起这一段情境,就会联想到人生总结一句话,就只是三个字:“来不及”。
(摘自《青田街七巷六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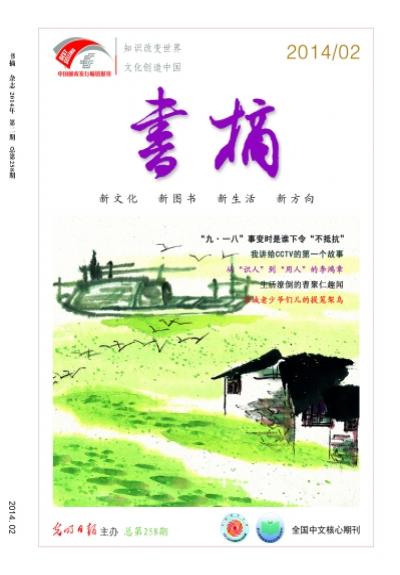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