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闲暇之时,好参诸杂学,或鸡零狗碎,或边角废料,不求博闻强记,只是为了明理,或为了寻觅一些自己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旨在随时“发兴”而已。然而毕竟学非《酉阳杂俎》,仰止《梦溪笔谈》,不敢求有《说郛》之宏大渊源,只愿参得《焚书》之半点皮毛,便也算是“夜航船门下走狗”,不枉此生了。
入山记
酷暑时节,偶与友人驾车数百里入晋,欲登五台,于清凉山下行脚五日,略有断想。感而遂通,又不得要领,只在挥发山林与心学意气。经云:“百一生灭名一刹那,六十刹那名为一念。二十念名为一瞬,二十瞬名为一弹指。”所谓“念念不忘”。只数日间,心中情绪如浮云飘散,各种繁杂无聊之念头不计其数。摘引之曰“念头”。
山即上师。
第一日上山便遇雨,夜宿于山麓下某小客栈。窗外有山,雨中绿荫亭亭如盖。友人云: “来此处,本为会一位上师。上师就住在隔壁。”吾答曰:“我向来不喜以人为上师。既入山中,山即上师。”
一个补丁,尚可忍受。十个补丁,矫揉造作。
半山上那个穿百衲僧衣者,必是第一俗人。
五台山下沿途皆是化缘僧人,却不要斋饭,只要货币,令人大跌眼镜,真假莫辨。再往前走,塔院寺前店铺林立,有批发僧衣、念珠、请香、台蘑、法器、唐卡与首饰等。是人皆可买上一堆,剃个头自称和尚。如今汽车遍野,行脚僧却也多如牛毛。忽见有一满身补丁袈裟之僧在打手机,便仰天大笑,忽又放声大哭。
风中大树摇摆,却无言静穆,唯独树边烟囱最是颐指气使。
客栈后有山野农家,烟囱最多,半夜亦生火烧饭,煤气熏人,烟雾缭绕,无法入眠。论吐故纳新,我从不戒肉,如树不戒风。世上最该戒者,便是那本来一根土烟囱,却要假装做机器时代的大树。
携琴一张,不如听风声鹤唳。
登东台时未带琴,忘在客栈里了。不过并不遗憾。牛鸣、溪水与大风呼啸之声,正好可以为鹤鸣九皋之音也。过去讲“对牛弹琴”乃是第一境界。此刻我“无琴亦对牛而弹”,如何不能是奇特事?
喇叭声咽,喇嘛亲切。
在显通寺,隔壁喇嘛罗珠冉色仁波切云:“你们照相,我是个多余人。”小群曰:“你不太多余。”喇嘛大笑。因他很爱照相。凤林禅寺有个老和尚,也爱照相。看来一切空相,并不耽误人们喜爱色相。空相越深奥,色相越亲切。
如何是境中人?台蘑炖土鸡。
一只鸡几个蘑菇278元。米饭8元。此汤喝不喝?棒喝。
见妻儿在寒冷山涧处采花、悬崖泥泞上拾草,如见菩萨。
正所谓“寒山文殊,拾得普贤”。
“无所事事”本身也是事的一种形式。
无聊处,且抄金人词一首:“几番冷笑三闾,算来枉向江心堕。和光混俗,随机达变,有何不可。清浊从他,醉醒由己,分明识破。待用时即进,含时便退,虽无福,亦无祸。
你试回头觑我,怕不待峥嵘则个。功名半纸,风波千丈,图个什么?云栈扬鞭,海涛摇棹,争如闻坐。但尊中有酒,心头无事,葫芦提起。”(李纯甫《水龙吟》)
我如今亦最爱吃“烂熟之物”(如张爱玲)。
尤其是淮扬狮子头、老黄酒烧肉、豆腐乳糟鱼;再如地方小镇、一张破琴、过气诗人。
路边鸟残乃万古人心。
归途中,于高速服务站广场上,见一死麻雀,头爪血肉模糊,然其尸翩翩若舞,令人想起佛经中的“鸟残”(鸟兽互相啄食后残留之尸骸腐肉)。因《楞严经》以不见杀、不闻杀声、不为我杀、自死、鸟残等为“五净肉”,僧人亦可食。不过此雀之死姿,实在令人感叹。现在即便是僧,也不会吃此类物罢。时过境迁,所有的理论都是幌子。所谓行善,也都是为了给自己贴金。
无限恨
折扇幽美,犹恨其出自东瀛之说。
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载:“古人用团扇,折扇出自朝鲜,日本之制。案《通鉴》云:‘褚渊入朝,以腰扇障目。’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
虽茶、水、人俱好,饮茶时,亦有十恨:
一恨茶室存香;二恨杯盏丑陋;三恨坐榻歪斜;四恨茗气交杂;五恨邻居炊烟;六恨窗前喧嚣;七恨对饮咂舌;八恨反复续水;九恨庸夫谈壶;十恨久坐不去。
以上为我多年前开琴馆时,每日应酬闲杂人等往来之心得也。
吾女核桃长大后,必视金钱如粪土。
如张岱《夜航船》云:“核桃与铜钱同嚼,则钱易碎。”
吃老灶火锅而无牛油,如读志怪而不见鬼神。
如今街头火锅皆为地沟油加味精,着实令人厌恶。
不恨奔鲋炊饭,可恼一生坐班。
清初诗人叶燮因生活困苦,有《奔鲋集》和《炊饭集》。但其心自由,虽受制于康熙满人之压抑,亦与今人因谋生不得不在单位终生坐班,尸位素餐者不可同日而语。
晨起饮茶,如洪钧赋与;临睡洗脚,即道在是矣。
叔本华曾告诫我们:“中产阶级必将因对幸福的厌倦而永远充满烦恼。”他也许是对的。不过中国人对生活毕竟与西方人不同。思想可以悲观,但言行却要乐观。清晨重读《伊川击壤集》,弹灰古籍,反照柔情,观物自省,追思命运,依然会感叹邵子的伟大境界:“道在是矣。”
我愿以厌倦为师,为夫妻,或以厌倦为伍,为友,为兄弟,乃至厌而不倦,崇拜厌倦。
诗境要轻若凌霄,诗学要重似托塔。
如清人沈德潜曾被尊为“乾嘉诗坛之托塔天王”。
诗人最恨量小,美人最恨臀小。可她既不美,又臀小,却仍爱生气与写诗。
若遗《尚书·太甲》云:“天作孽,犹可救;自作孽,不可活。”
大雪时节,最恨不能临窗涮肉痛饮酒。
寒气与热汤共舞,可谓冰火风流。而韩愈言“无以冰炭置我肠”,是小气之言也。
够他们“忙活三百年”有甚奇特?中国人为了几个注释已忙活了两千年了。
当詹姆斯·乔伊斯写完并出版了《芬尼根的守灵夜》后,对媒体云:“此书够他们忙活三百年了。”乔伊斯确是语言天才。不过其书除了借助民谣、爱尔兰史诗、意大利学者维科《新科学》的文明分类与近代性心理学之外,主要多以大量的词语(各种语言与典故)注释解构其复杂性。此类写法,吾国吾民自汉儒至清末朴学以来,便存有大量文献,所谓训诂索隐而已。即便不论学术,单论小说,金圣叹、脂砚斋等也早已划时代而为之,不足为奇也。
晨起读书,饮岩茶一壶,午餐又食宣威火腿,入夜后,则与宇宙抵足而眠,此等生涯遂不复寂寞矣。
冬日,收云南琴友赠新鲜宣威火腿一块,食之大美,只恨无滇中米酒相佐。
恨一灯红小,明月霸道,亦敌不过这清晨黑暗的曙光。
每日字不写、琴不练、画不涂,也能悠然自得,身宽体胖者,必然是没有烦恼了。世间事多属无常,唯专心读书,待机而动是根本。唯棒打妖魔,斗酒品茶最痛快。故纸堆中寻真主,琉璃盏中煮佛陀。黑夜孤独,一灯红小时,敢与神秘虚无之精神独来往者,方可称烈丈夫。世俗中秋,以满月为刀,能杀尽一切非方圆不成之规矩者,是为真快活。
癖海试勺
人为何物
张潮《幽梦影》曰:“蝇集人面,蚊嘬人肤,不知以人为何物?”张竹坡云此言为南华精髓。更有人言腥膻、腐肉、丑身等等。在我看来,此类事确是世间生物之癖好而已。万物之初,与人大同,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习之浅者,文明风俗也;习之深者,个性癖好也。而世间之人不如蚊蝇者,又岂在少数?故陶安公之警语数百年来振聋发聩:“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倪瓒洁癖笺
元人倪瓒生而有洁癖,却死于污秽,暂记其行事并眉批如下:
1.造香厕(一座空中楼阁般的厕所),以香木搭架子,下填土,上铺洁白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
批:西人以鹅毛笔写书,而倪瓒则用来掩盖粪便,其势然也。
2.仆人挑水来煮茶时,倪瓒只取前一桶,后一桶扔掉。问其所以,曰:仆人或许放屁,会污染了后一桶水。
批:此说奇特。只不知倪府是否需每日买桶,倪府人是否每日需换裤子。
3.某友人夜宿倪家。倪恐其不净,一夜巡视三四次。听得友人咳嗽,倪便一宿未眠。待天亮,急命仆人四处寻其友所吐之痰。仆人找不到,只好找来一片有污迹之树叶冒充。倪捂住鼻子,令仆人快送至三里之外丢之。
批:敢问世间何人能与倪瓒为友?咳嗽就是罪过。
4.倪瓒因得罪朱元璋而下狱时,对送饭的牢头云:须将碗筷举过头顶,因怕有唾沫污染饭菜。狱卒大怒,干脆将倪瓒锁在尿桶边,夜夜闻尿。后有人求情方得免。
批:倪瓒只是罗汉,牢头才是活佛。
5.元末时,“吴王”张士诚、张世信来求画,倪瓒不从。张氏大怒,打了倪瓒几十鞭,并指其欲杀之。倪瓒挨打时也一言不发。问其所以,曰:“一说便俗。”
批:一批便俗。
蹲食海碗
旧时北方国人粮食有限,却都爱蹲在街边墙角,抱吃一大海碗汤面馄饨。其实碗中面并不多,其妙在蹲食易饱。因大腿能挤住肠胃。
糖僧
晚清诗僧苏曼殊爱吃冰,但因尤其癖好甜食,故自号“糖僧”。据说曼殊二十来岁往东南亚游历,每日食五六十枚甜果,肠胃炎发作,几乎客死。他自记在杭州曾“日食酥糖三十包”。据周越然回忆,他最爱吃蜜枣,“有一次,他穷极了,腰无半文,他无法可想,只得把金牙齿拔下来,抵押了钱,买蜜枣吃”。
大蒜杀蚊
儿时的夏天,我父亲不喜点蚊香,而是爱将大蒜汁涂在身上或腿上,蚊虫莫近身。不过其他人也不愿近身,因蒜味刺鼻也。
(摘自《随身卷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定价:48.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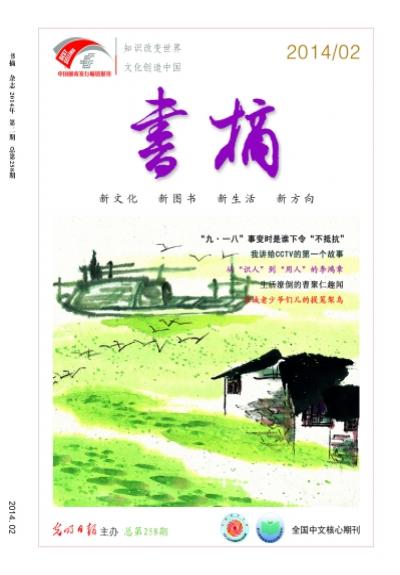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