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你父亲这一代,学者教授很多,最出名还是你父亲。
周:所谓出名,就是他恰好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全国最好的高校。至于学术水平有多高,至少在北京大学那个环境下,他没有好好做学术,不断参加运动。
丁:你父亲的学术专长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但在社会上造成影响的却是他主编的《世界通史》。
周:好像是1961年,周扬主持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工作,历史组翦伯赞是组长,父亲是几个副组长之一。当时国家不需要对于魏晋南北朝的深入研究,需要给大学生提供一套世界史教科书,于是抽几个人来编。父亲曾留美,英文没有问题,编这个书至少英语得过关,所以抽了他和吴于廑等人,吴也是留美的。这个书被用了不少年。
丁:到“文化大革命”后还用呢。那时候也没有别的教材。再早是翻译了一套苏联的《世界通史》,中国的《世界通史》基本上是把人家的东西浓缩一下。
周:对,肯定不会有自己个人独创的思想,对世界史应持什么观点,苏联已经做出榜样了,就照猫画虎来吧。
邢:这个通史成为高教部指定的教材。上世纪60年代初,周扬提出搞一套文科教材,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意识形态。
(丁:当时搞出这么一套教材,全国各高校都要学。)
周:是偶然成就了他的名气,当时父亲找了吴于廑,吴于廑名气比他小,实际上主要的工作是吴于廑承担的。后来父亲跟我说,他一直愧对吴先生,就因为他的名字排在了吴于廑前面。吴于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骨干,和父亲同岁,曾与他几乎同时在美国留学。
邢:在世界史领域,你父亲主要是撰写亚洲史。
周:对,除了英文,他还会日文。
丁:你父亲在学术上是怎么被胡适看中的?
周:胡适跟祖父周叔弢有些互相借阅、交换藏书这方面的来往。我在父亲的检查里看到过,说胡适跟自己家的长辈过去是有交往的。
胡适对于当时中国大学文科毕业生中的苗子都比较注意。傅斯年是当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头,也注意看应届毕业生里有没有值得引进到所里的人。我见到过的文字是1946年前后傅斯年给胡适的信,提到有个周一良,从美国学成快回来了,这个人得抓住,别让其他单位弄走,给他一个教授当也值得。2009年我去了一次台北,2011年9月初又去了一次台北,看当年中研院的档案和傅斯年的私人档案,找出我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写给傅斯年的信,但傅斯年的回信没有全部保留下来。他把正式文函寄给我父亲了,底稿有的留着,有的没留,所以不完全。只能推测,傅斯年对父亲很器重,希望他来。父亲1939年去美国留学,用的钱是燕京大学提供的,燕京大学每年资助一名中国文史学科的学生到哈佛读博士。当时已经形成惯例,哪儿派出去的,回来就到哪儿服务,除非派出单位不要你了。所以他还是先回燕京,在燕京待了一年多。由于欣赏他的洪煨莲在美国,而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对他不是很器重,也不给他分房子。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只能住在天津祖父家。我哥哥是1939年生的,父母出国后,一直留在祖父身边长大。父亲一直住在单身宿舍,想和太太、俩孩子在燕大校园团聚,但燕大迟迟不给房,于是他生气跳槽就到了清华。按说,他跳槽应该首选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他觉得1936年到1937年在史语所那一年是最高兴的,也是最能施展其学术能力的一年。可能是带着老婆孩子到南方不方便吧,于是他联系了清华。清华历史系马上就要了他,许诺给他一座小楼住。所以,他1946年11月从美国回来后,在燕京教了两学期,1947年年底就到了清华,把我们都接来了,他一直在清华待到院系调整。
丁:1949年以后,他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早入党的,和你祖父有没有关系?
周:我觉得有。我祖父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历史上没有过任何与共产党对立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也愿意跟新政权合作。清华其实比北京市早解放了几乎一年,1948年北京西郊已经是解放军的天下了。在国民党军队撤走、解放军还没进学校时,清华组织学生巡逻队护校,夜间巡逻全校,包括住宅区。全校教授每家都准备茶水夜宵之类,让巡逻队进屋休息。我爸爸有一本房客签名簿,但凡来客都请留名,上面还有艾知生、朱镕基巡逻到家的签名。那会儿清华积极要求革命的教授没有我父亲。当时是周培源、钱伟长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东奔西跑,喜形于色。我有一个最小的叔叔,当时是清华物理系学生,作为目击者,亲口给我讲了周培源、钱伟长兴奋的样子。当时多数人是忐忑不安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都保持低调。我父亲在考虑自己走不走。后来他决定不走。我祖父给他寄了一些钱,说政权刚交替,生活会有一些困难,给他一些钱应急。他不走是肯定的。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也不在国民党抢救的范围之内,不会给他飞机票。他“海归”刚回来两年,年资和名声显然不够。能拿到傅斯年提供的机票的都是比他大十多岁的上一代人,是他的老师。
他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共产党视野?我也试图作一些了解。现我所知的,一个是谢泳给我的1955年的高教部文件,清华北大知识分子调查报告,里头直接点名说周一良年纪比较轻,历史清白,愿意靠近共产党,是培养对象。说明那会儿他的言论和行动被认为是积极靠近共产党的。在这之前,他怎么开始接受新政府的现实;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怎么成为共产党眼里的进步知识分子、培养发展对象,中间过程他从没跟我亲口说过,我也没看到其他文字材料。只有他一个学生跟我说,周先生自己检查时说过,一开始对共产党认识不深,有恐惧心理,觉得他那样的家庭,那样的人,不知共产党来了还能不能让他接着教书。若丢了教书的饭碗,他得准备去蹬三轮。在检讨会上这样说,属于交心。其他再具体的东西我也说不出来了。其实那时清华北大教授、高级知识分子,肯定是各有各的担忧或期望,可是我始终没能看到更多的具体材料。
丁:他在学术转换方面有过什么困难吗?他的转换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周:我后来看了他的思想汇报,说决定跟着共产党走,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组织让干啥就干啥。需要亚洲史,而且要亚洲近现代史,跟魏晋南北朝完全不搭界,但既然是组织需要,那就干。至少是从50年代开始,他就这样了。直到晚年,他还坚持说,新中国史学比民国史学高明之处,就是有了辩证唯物主义,1949年他年轻,接受新鲜事物不像老年人抵触那么大。
邢:周一良是哪一年入的党?
周:1956年成为预备党员,常规应该是一年转正,结果1957年反右当中,好朋友丁则良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很悲痛,跑去绕棺一周,还哭,被认为立场不坚定,一年到期没给转正,这给他一个很大的警告。到1958年年初转了正,实际已经是破例了。
丁:你父亲不但入了党,还当过北大历史系副主任,是不是他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呢?
周: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行政能力的。他在清华历史系早就当过一届系主任,1950年到1951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他就是清华历史系的系主任。他是带着主任的头衔到北大来的。清华的传统跟现在美国的传统一样,系主任是一个给权威们跑腿的差事,很多教授不爱干,所以你一届,我一届,轮着干,没有连任的。
邢:你父亲进入“梁效”以后,你们家族里的人怎么看?
周:明眼人都知道这事风险大,但跟他说,他听不进去。多数亲戚看他的积极性挺高的,就不说了。只有一个人正式跟他说了,就是我的大姑父宁致远。宁致远是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也代任过副部长。他对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是很清楚的。他作为我祖父周叔弢的女婿,祖父周叔弢到北京来,北京所有儿子、女儿都带着孩子去看望,他不去,只让姑姑带着我的表弟表妹去。宁致远和在北京周家的内弟内妹之间来往不多,一般都是这些兄弟姐妹上他家。可是这次,姑父宁致远亲自跑到北大来,跟我父亲单独见面,就说了四个字:急流勇退。我爸没听懂。这是“梁效”最红的时候。
邢:“急流勇退”还听不懂?
周:或者是听懂了,决定不接受。宁致远一直为中共做地下工作,在延安也待过,经历过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跑到姑姑家,问现在共产党整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姑姑说,你不知道,延安时比这会儿还厉害呢。这都是姑姑跟我说的。姑父从来不说这些,跟自己的孩子也不说,不写任何回忆录。我后来对他儿子说,你爸应该写点回忆录,他有很丰富的经历。他说,我爸说不写,什么都不留下。可能是伤了心,地下党很多人后来处境不好。
丁:打倒“四人帮”后,你父亲走了背字,亲戚们对他怎么样?
周:祖父周叔弢的10个儿女有五六个党员,九叔比较年轻,说大哥这一步是在浑水里蹚了一次,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为他担心。至于公开表示划清界限的,倒没有。
他被审查两年多。“梁效”活动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学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效”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邢:他直接跟江青打过交道吗?对江青印象如何?
周:这个他守口如瓶。我想单独谈话肯定是有的。作为文史方面的顾问,江青如果忽然想到一个什么事,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打电话或者见面,都不排除。这几个老教授随叫随到,谈些历史典故什么的,但他在检查里也没说哪天跟江青谈过什么话。
他检查里说,曾经觉得江青这个人,堂堂领导,说话这么随便,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好伺候,但是马上就提醒自己,不应该这么背后评论人家。
(摘自《小谈往事》,中信出版社2013 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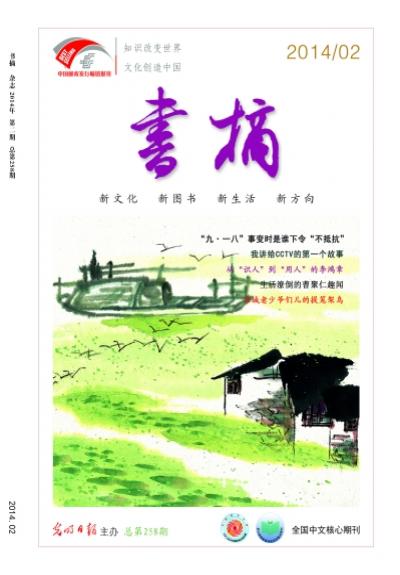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